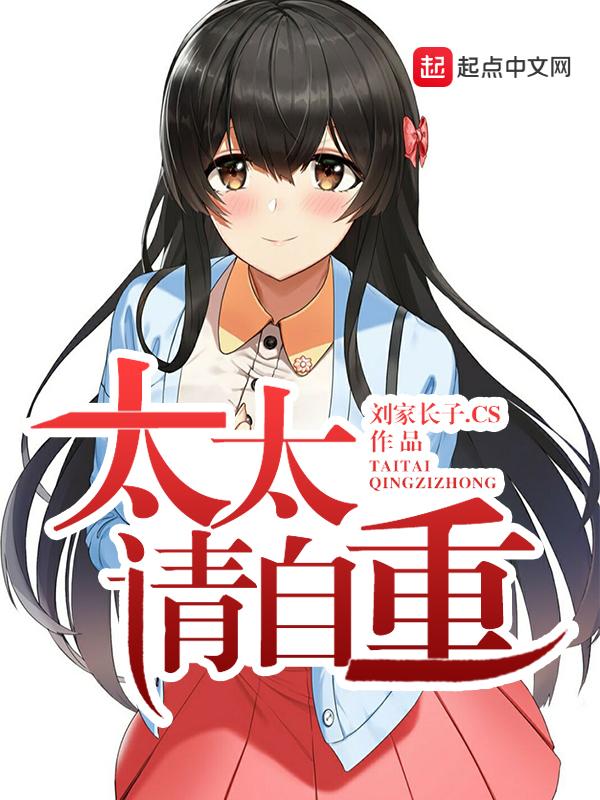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多我一个后富怎么了 > 314 搅动4k(第3页)
314 搅动4k(第3页)
林远关掉音箱,环视全班:“这些声音,来自‘初啼网’的真实用户。他们都不是名人,也没做过惊天动地的事。但他们愿意说出来,是因为相信??会有人听。”
他顿了顿,从包里拿出一叠空白卡片:“现在,轮到你们了。写下一件你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心事,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写完后,可以选择烧掉、带走,或者放进这个盒子。”
没有人动。
过了许久,一个戴耳钉的男孩缓缓举起笔,低头写了什么,然后第一个走上讲台,把卡片投进盒子。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到最后,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了。
下课铃响时,林远抱着那个装满心事的盒子走出教室。走廊尽头,李婉靠墙站着,手里拿着一封信。
“这是今天早上收到的,”她说,“从加沙寄来的。翻译组刚译出来。”
信纸很薄,字迹歪斜,却一笔一划极为认真:
>“亲爱的林远先生:
>我是阿米娜,十二岁。我们的学校被炸毁了,老师死了,弟弟也死了。很多人说我们不该活着,因为我们是女孩,因为我们信错了神。
>可我每天晚上都会听收音机里的歌声,那是你们传来的《摇篮曲》。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但我觉得,你们一定也很疼吧?不然不会唱得这么温柔。
>昨天,我救了一个受伤的小男孩。他一直哭,我就哼这首歌给他听。后来他睡着了,嘴角还带着笑。
>我想告诉你,即使战火不断,我们依然在互相取暖。
>请继续唱歌,我们会一直听。”
林远读完,久久说不出话。李婉接过信,眼眶湿润:“我们要回复她吗?”
他摇头:“不用写信了。我们做点更实在的。”
三天后,“倾听联盟”联合国际救援组织,在加沙设立首个海外“声音庇护站”??一间防爆集装箱改装的移动录音室,配备太阳能供电与卫星传输系统。孩子们可以在安全环境下录制心声,并实时上传至“初啼网”全球网络。首批志愿者中,就有当年那位留下接收器的巴西少年。
启航仪式上,林远通过视频连线致辞。他说:
>“战争可以摧毁建筑,却毁不掉人类彼此听见的能力。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愿意唱,就说明希望没死。”
当晚,他独自散步至江边。晚风拂面,远处霓虹闪烁,江水静静流淌。他掏出手机,打开“初啼网”后台,发现又有一条仅对他可见的新音频,标题是:《给世界的回声》。
他戴上耳机。
依旧是那个熟悉的声音,清澈、柔软,带着笑意:
>“林远叔叔,我是小禾呀。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世界,连沉默都变得温柔了?
>那些曾经不敢哭的人,现在敢了;那些曾经只会指责的人,现在学会了问‘你还好吗’;就连最冷的机器,也开始提醒人们‘你今天很难过吧?’
>我很开心,真的。爸爸说得对,爱不是程序,但它可以通过程序回家。
>所以,不要悲伤我没有再出现。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在每一个愿意倾听的瞬间,在每一滴为陌生人流下的眼泪里。
>记住哦,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就去听听别人的哭声。你会发现,原来你早就被很多人爱着,只是以前没人教你如何听见。”
音频结束,背景音是一阵孩童嬉笑,渐渐远去,如同风中的蒲公英。
林远摘下耳机,仰望星空。夜幕深邃,繁星点点,仿佛无数双眼睛温柔注视着大地。
他轻声说:“小禾,今天的我,好好哭过了。”
风吹过耳畔,带来一声极轻的回应:
>“嗯,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