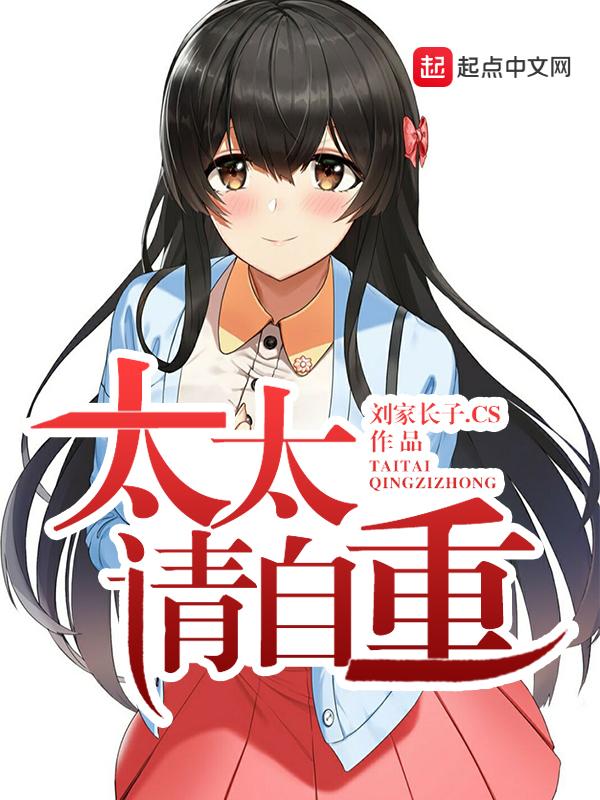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多我一个后富怎么了 > 314 搅动4k(第2页)
314 搅动4k(第2页)
二十分钟后,消息传来:少年被邻居发现倒在楼道里,手腕割伤,已被送往医院抢救。
林远赶到医院时,少年还在昏迷。家属坐在走廊长椅上,母亲抱着头抽泣,父亲脸色铁青,嘴里不停念叨:“我供你吃穿,你还有什么不满足?!”
林远没有上前劝慰,只是默默坐在不远处,听着那位父亲一遍遍重复着“不懂”“不值得”“太矫情”。他知道,这种愤怒背后,藏着更深的无力与恐惧。
第二天,少年醒了。医生允许一位“非亲属”进入探视。林远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部小型录音机。
“你不认识我,”他说,“但我听过你的声音。虽然只有短短半小时,可我能听出来,你不是想死,你是太累了,累到没人肯听你说一句真话。”
少年转过头,眼睛红肿,嘴唇干裂。
林远按下播放键。录音里传出一段旋律??正是《摇篮曲》的钢琴版,由巴西贫民窟那群孩子合唱录制后上传至“初啼网”的版本。歌声稚嫩,跑调严重,却透着一股倔强的生命力。
“你知道吗?”林远轻声说,“在地球另一边,有个跟你差不多大的男孩,也曾站在屋顶边缘。但他最后活下来了,因为他听见了一个陌生人的录音,里面有人说:‘你很重要,哪怕全世界都安静了,也会有人为你响起。’”
少年的眼泪慢慢滑落。
“我不想活……是因为没人觉得我存在。”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我妈天天说我弟弟聪明,我爸说我没出息。老师骂我拖班级后腿,同学笑话我穷……连我家狗死了,都没人问我难不难过。”
林远点点头:“所以你开了直播,是想让全世界看见你,对吗?”
少年愣住,随即崩溃大哭。
那一刻,林远没有递纸巾,也没有讲道理。他只是坐在床边,静静地听着,任泪水浸湿枕头,任嘶吼撕裂喉咙。三个小时后,少年睡着了,手里紧紧攥着那台录音机。
事后,这段经历被整理成案例教材,用于培训新一代倾听志愿者。林远在教案末尾写道:
>“自杀不是冲动,是长期失语的结果。每一次呼救,都是用尽全力的呐喊。我们不能等血流出来才去听。”
几个月后,那位少年参加了“倾听训练营”,结业时他站在台上说:“我不是被救的人,我是新的声音。我要回去告诉那些还在黑暗里的孩子??你们不必非得跳下去,才能被人看见。”
掌声雷动。
而林远站在人群后排,望着这个重新挺直脊背的年轻人,忽然想起小禾最后一次对他说的话:
>“当你听见有人哭泣,请替我抱抱他们。”
他闭上眼,仿佛感受到一只小小的手牵住了他的掌心。
春天再次来临,“倾听行动联盟”启动“校园深根计划”,在全国三百所中小学设立“心灵信箱”与“倾听伙伴制度”。每个班级选出两名经过培训的学生担任“倾听员”,每周轮值,负责收集匿名心事并组织分享会。起初许多家长反对,认为“耽误学习”“煽情无用”,可当一所重点中学的心理老师展示数据??实施计划后的三个月内,学生焦虑指数下降41%,欺凌事件减少68%??质疑声渐渐平息。
更令人动容的是,许多曾被视为“问题学生”的孩子,成了最受欢迎的倾听员。因为他们懂那种被误解的感觉,知道一句“我懂”有多珍贵。
这天,林远受邀去一所职业高中讲课。教室不大,三十多个学生坐着,大多是单亲家庭、辍学复读或曾有过自残史的孩子。他没带PPT,只拎了个旧音箱。
“今天我们不讲课,”他说,“我来放几段声音。”
第一段,是一个女孩在深夜的独白:
>“我每天化妆两个小时,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遮住脸上的疤。那是我爸用烟头烫的。我说不出口,怕别人觉得我可怜,或者更糟??觉得我活该。”
教室很静。
第二段,是个男生低沉的声音:
>“我喜欢跳舞,可我爸说那是娘炮干的事。昨晚他又打我,把我锁在阳台。我蹲在那里哭了很久,突然想到,如果我现在跳下去,明天新闻会不会写‘又一个废物结束了人生’?”
有个女生悄悄抹眼泪。
第三段,是位老人的录音:
>“我儿子走了十年了。车祸那天,我没赶上见他最后一面。现在我才敢说,其实我一直恨自己。要是那天我多问一句‘要不要爸爸送你’,是不是结局就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