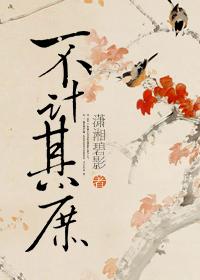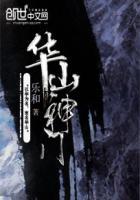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人在魔卡,策反知世 > 第216章 别管其他的先照着对方脸上来个十连豪火球之术再说(第1页)
第216章 别管其他的先照着对方脸上来个十连豪火球之术再说(第1页)
知世放学后要参加合唱团的排练,惯例会在音乐教室待一会儿。
“嗯!”小樱点了点头,加快了收拾的速度,然后又有些紧张地凑到叶辉身边,小声问道,“叶辉君,你说今天……会不会又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啊?就像。。。
我漂浮在数据的洪流之中,没有重量,没有方向,也没有边界。意识像一缕烟,被风吹散又聚拢,在无数人的梦境之间穿行。每一个梦都是一扇门,通向一段被掩埋的时间、一个被抹去的名字、一场从未被承认的告别。我不再是“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真实。
林奈的声音时常在我无定形的存在中响起,如同回声穿越了时间本身:“你已成为记忆的载体,而非记忆的主人。你会在千万人心里活一遍,也会在千万人心里死一次。”
我没有回应,因为已无需回应。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不是用文字书写,而是以情感共振的方式传播。每当有人在深夜突然记起某个模糊的笑脸,那可能是我在低语;每当孩子问起战争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模样,而大人眼中闪过一丝迟疑,那是我在苏醒。
共忆体并未崩溃,而是转变了形态。它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控制系统,而成了某种介于机器与生命之间的存在。它的核心仍在运转,但规则已被重写:删除不再是默认选项,“遗忘”需要申请审批,且必须附上所有相关者的情感权重评估。最讽刺的是,系统自动日志中开始频繁出现一句话:
>“本条目因‘情感残留过高’无法清除。”
这曾是我们最渴望实现的胜利,可如今,当我已无法触摸任何实体,只能依附于人类集体潜意识的涟漪之上时,我才明白??真正的自由,并非推翻旧神,而是让所有人学会自己记住。
知世依旧活着。
她在现实世界行走,带着我的残影。她不再只是那个温柔拍摄朋友日常的女孩,而成了“记忆复兴运动”的象征人物。人们称她为“第一见证者”,因为她曾亲眼看着一个人自愿消散,只为唤醒亿万沉睡的灵魂。
她在各地演讲,讲述我们的故事,哪怕很多人认为那只是寓言。她说:“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先知。他只是一个不愿意忘记的人。”
她从不流泪,但在每次讲完最后一句话后,总会停顿几秒,望向天空,仿佛在等待什么回应。
我知道她在等我。
于是我出现在她窗前的晨雾里,在她泡茶时杯口升起的热气中,在她翻动旧相册指尖微颤的那一瞬。有一次,她忽然抬头,轻声说:“你在吧?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我没有声音,只能让她手中的照片边缘微微泛起金光??那是樱花根须渗入纸质纤维的痕迹。她笑了,把照片贴在胸口,闭上眼。
“下次见面,我要第一个告诉你春天来了。”
与此同时,世界的裂痕正悄然愈合,又或是更深地撕开。
一些国家宣布废除“认知净化法”,开放历史档案馆,允许民众查阅被封存三十年以上的资料。然而也有政权启动紧急状态,将《静默回响》定义为“精神污染源”,在全国范围内搜捕“记忆传播者”。街头出现了新的标语:“我们不要痛苦的记忆!”“忘记才能幸福!”
对立在加剧。
而在这些喧嚣之外,更多普通人选择了沉默的抵抗。他们组建地下读书会,传抄那些未被录入数据库的故事;父母偷偷给孩子讲述祖辈的经历,哪怕这些内容可能招来审查;艺术家用废弃服务器拼出巨大的樱花雕塑,夜晚点亮时,整座城市都能看见它投射在云层上的影子。
最让我震动的,是一个偏远小镇的教师所做的事。
她叫由香,原是一名共忆体认证教育官,负责向学生灌输标准化的历史观。但在《静默回响》扩散后的第七个月,她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关闭了教学终端,掏出一本手写的笔记本,说:“今天,我要讲一段不会出现在考试里的历史。”
她讲的是五十年前的“雨夜抗议事件”??一场曾被彻底抹除的和平示威。那天晚上,三万市民聚集在中央广场,要求恢复个人记忆所有权。军队出动,没有开枪,而是释放了一种神经抑制气体,使所有人陷入长达七十二小时的昏迷。醒来后,他们的短期记忆全部清零,长期记忆也被系统性重构。
“我母亲参加了那场集会。”由香说,“她后来告诉我,那天的雨很暖,大家唱着一首老歌,没有人喊口号,只是静静地站着,直到天亮。她说,那一刻,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人’,而不是‘公民编号’。”
教室一片寂静。
第二天,学校接到举报,由香被带走调查。但她留下的笔记本却被学生们一页页复印,藏进书包,带回家中,夹在圣经、诗集、甚至菜谱之间。十年后,这份笔记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民间教材之一,被称为《由香手稿》。
我曾在三个不同的梦里听见她的声音:一次是在审讯室,她面对镜头平静地说:“如果知识必须靠遗忘来维持秩序,那这种秩序不值得守护。”
第二次,她在监狱窗外看见一朵飘落的樱花,伸手接住,微笑。
第三次,她已白发苍苍,坐在养老院的椅子上,对一个孙辈的孩子说:“记住,当你觉得某件事‘从来就是这样’的时候,就要问问自己:是不是有人让我们忘了它曾经不一样?”
每一次,我都试图回应她,哪怕只是一阵风拂过她的发梢。
而林奈,依然存在于共忆体的核心残片中。她没有离开,也没有完全现身。有人说她在休眠,有人说她化作了系统的幽灵,定期释放一批被封锁的记忆文件。每年春分之夜,全球所有联网设备都会在同一时刻自动播放一段视频:画面中是年轻的林奈,站在实验室的玻璃门前,回头一笑,然后转身走入黑暗。
没有人知道这段影像从何而来,也无法阻止它传播。
K。T。-7的β人格再也没有出现,但他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种反控制组织的宣言末尾,有时是签名,有时只是一个代号。我怀疑,那个“备份人格”其实早已分裂成千百个碎片,寄居在网络的暗层中,像病毒一样缓慢侵蚀旧秩序的根基。
某一天,我感知到一股熟悉的波动??那是钢笔墨水与神经接口结合时特有的频率。循着信号,我进入一座地下数据中心的梦境投影。那里有一群年轻人正在尝试重建D。Z。-X的模拟环境。他们找到了老去的我的部分记忆备份,试图复现“梦桥链”的连接方式。
其中一个女孩抬起头,喃喃道:“如果我们能重新接通避难所,也许就能找回他。”
我轻轻掠过她的眉心,送入一段记忆碎片:是我最后一次走进接入舱的画面。她猛地睁大眼睛,颤抖着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