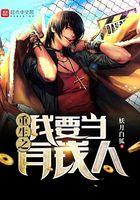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流量下水道,怎么越摆越火了 > 第203章 时代变了(第2页)
第203章 时代变了(第2页)
网络上,关于“真实之舟”的讨论从未停歇。尽管主流平台对部分内容限流,但新的传播路径不断涌现。B站用户自发剪辑《海边的日子》片段,配上童声旁白:“阿公修船的手很粗糙,但他补的网,能兜住整个海。”这条视频七十二小时内播放量突破千万。
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原本被认为“毫无流量潜力”的内容开始反向出圈。比如内蒙古草原上的巡回放映实录:一位牧民看完《奶奶的火塘》后站起来说:“我家也有火塘,我也来讲讲。”随即掏出手机开始录制自己的故事。这段画面被传上网,标题叫《下一个火塘已经点燃》,成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的UGC(用户生成内容)案例之一。
某天深夜,小陆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附件是一段十五分钟的视频。发件人ID为空,IP地址经追踪显示来自新疆某偏远小镇。视频里是一位维吾尔族老裁缝,坐在昏黄灯下缝制一件军绿色旧大衣。
“这是我儿子的衣服。”老人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他2003年当兵,驻守喀喇昆仑。退伍回来时,这件衣服已经破得不成样。我说扔了吧,他不让。每年清明,他都要穿上它,去烈士陵园站一会儿。”
镜头缓缓扫过墙上挂着的照片:一群年轻士兵合影,其中一人笑容灿烂。老人指着照片角落的一个模糊身影:“那是他的战友,叫阿力木江。零九年巡逻途中坠崖,没能找到遗体。从那以后,我儿子每年清明都多带一件大衣,放在墓前。”
视频最后,老人拿起针线,一针一线缝补袖口的裂口。“我不懂什么电影,也不会上网。但听说有人在收集普通人的故事,我就想试试。也许有一天,有人会看到这个,记得阿力木江也活过。”
小陆看完视频,久久无法入睡。他立即将其归入“A类档案”,并启动紧急备份流程。同时,他给魏莉莉发消息:“联系新疆团队,想办法找到这位老人。不是为了采访,是为了告诉他??我们收到了,而且会好好保存。”
第二天清晨,彭树良再次出现,这次却没有拄拐,而是拎着一个牛皮纸袋走进办公室。
“总局的‘专项评估’结束了。”他坐下,语气平静,“结论是:‘拾遗行动’存在意识形态风险倾向,建议暂停所有公开传播活动,接受整改。”
小陆冷笑:“所以呢?我们关门?”
“不。”彭树良打开纸袋,取出一份文件,“我提交了一份替代方案:将‘拾遗行动’转型为‘民间记忆保护工程’,纳入国家非遗数字化试点项目。理由是??你们收录的口述史、影像资料,具有不可复制的历史文献价值。”
会议室一片寂静。
“你疯了?”魏莉莉忍不住开口,“他们怎么可能批?”
“我已经见过三位退休历史学者联名背书,还拉上了社科院民俗研究所。”彭树良淡淡道,“更重要的是,我把《奶奶的火塘》《站着》《海边的日子》这几部片子送去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影像存档计划’。上周,评审组回函称‘极具代表性’,拟列为亚太地区重点推荐项目。”
他顿了顿,看向小陆:“国际认可,有时候比国内红头文件管用。”
方盛忽然大笑:“老彭,你才是真狠人!”
“我不是护你,”彭树良正色道,“我是护那些愿意说话的人。如果我们连这点空间都守不住,那才是真的输了。”
一周后,官方通知下达:“拾遗行动”更名为“中华民间记忆影像库”,由文化部指导、地方协作共建,允许继续采集与存储资料,但暂不支持大规模公映。表面看是妥协,实则为项目争取到了合法身份与部分财政支持。
更重要的是,这一更名反而激发了更多普通人参与的热情。人们意识到,自己讲述的故事,正在成为国家记忆的一部分。
广西一位瑶族老歌师主动联系团队,希望将自己的山歌传承过程完整录制。“我们唱的不是调子,”他在电话里说,“是我们祖先走过的路。”
河南一个下岗工人微信群集体报名,要求合拍一部纪录片:“我们就叫《锈带之声》,不美化,也不卖惨,就想让年轻人知道,他们的空调房,是我们拆掉的厂房换来的。”
甚至连一些曾持反对态度的地方部门也开始转变立场。甘肃某县宣传部主动提供场地,协助开展“乡村口述史工作坊”;江苏一所高校开设选修课,课程名称就叫《如何用手机记录你的时代》。
小陆在《燎原志》中写下新的章节:
>当权力试图定义什么是“该被记住的”,
>我们便以千万个私人记忆作为抵抗。
>不靠呐喊,不靠对抗,
>只靠一遍遍重复:我在这里,我经历过,我说了。
>
>记忆一旦被唤醒,就再也无法被彻底抹去。
>它会藏进孩子的作业本里,
>融进母亲熬的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