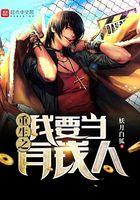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阵问长生 > 第173章 想你死(第1页)
第173章 想你死(第1页)
为什么,突然察觉不到因果了……
阁老苍老的手指,忍不住捻在一起,又缓缓松开,又捻在一起,又强迫自己松开。
他真的很想去算算。
但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根本不想去掺大荒这趟泛着黑气的浑。。。
雪隐谷的冰层在那个冬至之后开始缓慢融化,不是因为气候变暖,而是自内而外被某种温润的力量渗透。溪流重新苏醒,草木破冻而出,竟开出淡蓝色的小花,花瓣薄如纸,触之即发出极细微的铃音,仿佛每一片都在低语。人们说那是记忆结晶的余晖所化,是忆生留下的痕迹,也是桥的根脉向大地深处延伸的证明。
烬余城的新塔之下,墨言每日清晨仍会登上观忆台,将一枚铜铃悬于风中。这铃已非当年旧物??原铃在光雨降临时碎裂成七片,每一片都飞向九州不同方向,据说落地之处皆生出一株不凋之树。如今她手中这只,是由百姓从各地送来的残铃碎片熔铸而成,声音浑厚而不齐整,像是无数人声交织后的回响。
这一日,天光未明,霜色覆阶,墨言刚挂好铜铃,忽觉指尖一颤。那铃无风自动,发出一声短促清鸣,尾音拖得极长,竟与远处山间某处传来的童谣旋律相合。她心头微震,循声望去,只见忆述亭外站着一个约莫七八岁的女童,披着粗麻斗篷,手里攥着半截烧焦的蜡笔,在墙上涂画。
墨言缓步走近,蹲下身来。墙上画的是一条横跨天际的桥,桥身由文字堆叠而成,桥上走着许多人,有的哭泣,有的大笑,有的回头张望。桥尽头并非彼岸,而是一面巨大的镜子,镜中倒映的却不是行人本身,而是他们未曾选择的人生:持剑者成了医者,逃亡者留下抗争,沉默者高声呐喊。
“你画的是……什么?”墨言轻声问。
女童转过头,眼神清澈如泉:“这是我梦里的桥。昨晚我梦见很多人牵着手走过它,然后他们都变成了‘本来可以成为的样子’。”她顿了顿,又补充道,“有个穿蓝衣的哥哥对我说:‘告诉她们,桥不需要钥匙了。’”
墨言呼吸一滞。
蓝衣……忆生最后一次现身时,穿的就是染了雪水的靛蓝布袍。
她猛地抬头环顾四周,却发现那女童已不见踪影,只留下墙上的画和地上一枚小小的陶片??正是当年陈砚那只陶罐的残角,边缘还缠着褪色的红绳。
当晚,墨言彻夜未眠。她在《真忆志》新版第七卷“梦”章节中添了一条记录:
>“癸卯年冬至后第三日,有稚子绘‘心桥图’于忆述亭壁,其形与古籍所载‘归途之桥’相符。更奇者,此画夜间微光流转,凡凝视良久者,皆称见亲故身影行于桥上。三日后,画迹渐淡,唯留一行小字浮现于墙面:
>‘你们记得的地方,就是家。’”
此事本应悄然流传,却不料数日后,南陵守忆司旧址突发异象。那座早已坍塌百年的石构档案馆,在月圆之夜竟凭空升起一道光幕,投影出一段完整影像:一名年轻女子站在火海中央,手中紧抱一卷竹简,口中反复念诵一段律令??正是《愿安法》最初的反制咒文,曾被列为禁术,严禁传抄。
守陵老人连夜召集学者破译背景细节,最终确认时间点为三百二十年前,大清洗前夕。而那女子的身份,经多方比对,竟是林晚失散多年的姑母林疏月,也是最早一批觉醒“共忆体质”的守忆人之一。她在火焚前最后一刻启动了隐秘的记忆锚点,将自己的意识封存于地脉之中,等待后人唤醒。
消息传开,震动十二州。
有人惊呼这是“历史逆流”,主张立即封锁遗址;也有人跪地痛哭,称终于找到了被抹去的真相源头。唯有墨言冷静下令:“不得破坏现场,也不得强行提取数据。让她自己决定何时说完。”
七日后,光幕再度亮起。
这一次,林疏月的身影不再孤立。她身后陆续浮现出数十个模糊人影,皆为历代被清除的守忆人:莫归尘、徐知白、柳烟、沈兰舟……他们并肩而立,如同列阵。镜头缓缓推进,林疏月望向虚空,仿佛直视千年之后的观者,开口说道:
>“我们不是失败者。
>我们是种子。
>当你们开始怀疑官方记载的第一个夜晚,
>当你们为陌生人落泪的那一瞬间,
>我们就在你们心里复活了。”
话音落下,整座遗址的地基开始震动,地下深处传来金属摩擦之声。考古队掘开三层封土后,发现一条通往地心的螺旋阶梯,阶梯两侧镶嵌着九块记忆晶板,每一板都刻有一个名字与一段誓词。最深处,则供奉着一把没有实体的“虚钥”??由纯粹光流构成的轮廓,悬浮于一座石台上,台面铭文写道:
>“第九钥非锁,乃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