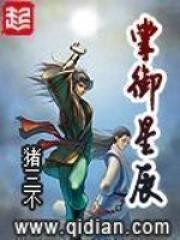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装傻三年:从状元郎到异姓王 > 第六百七十九章 罢免沈浩王爷之位(第2页)
第六百七十九章 罢免沈浩王爷之位(第2页)
他立即召集所有留居村中的寻声者,宣布一件大事:“我要建一座‘无声堂’。”
众人不解。
“不是用来听的,”他说,“是用来不说的。”
选址就在桃树对面的荒坡。建筑材料不用砖瓦,全由村民亲手编织的竹篾与夯土构成,墙体夹层中埋入特制陶管,形成天然共鸣腔。屋顶设计成螺旋状,中央留孔,直通天穹。内部无座椅,只有环形地台,可供人盘膝而坐。
“这里不许演讲,不许训导,不许传播任何所谓真理。”沈知白立下规矩,“只允许一个人来做三件事:坐下,闭嘴,感受自己的心跳。”
七月流火,无声堂竣工。落成当日,沈知白携阿音步入其中,点燃一盏长明灯。火焰跳动之际,整座建筑发出轻微嗡鸣,如同深海回响。几个孩子好奇触摸墙壁,竟听见自己昨日咳嗽的声音从另一侧传出,清晰得令人战栗。
“它记住了。”阿音whisper。
自那以后,每逢朔望之夜,总有人自发前来静坐。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整整一夜毫无动静。但离开时,大多眼神清明,仿佛卸下了多年重负。
与此同时,外界局势急转直下。
八月十五,中秋夜。京城传来噩耗:那位曾收信的退休御史,在家中暴毙,死状诡异??双耳流出黑色黏液,耳道内发现微量金属粉末。官方宣称其“年老体衰,突发恶疾”,但知情者皆知,此人последние公开言论是呼吁废除“清音营”,并提议立法保护“沉默权”。
沈知白焚香祭拜,随后将第九书之钥再度深埋,这次置于无声堂地基之下,与四根主柱同深。他在石匣外刻下八字:“声出于寂,道归于无。”
九月末,朝廷终于出手。
一支由十二人组成的“礼乐巡查使团”抵达山村,声称奉旨考察民间音律传承,实则携带精密仪器,暗中扫描全村居民脑波与听觉反应。他们假借采风之名,录制村民对话、歌声、咳嗽声,企图捕捉异常频段。
沈知白不动声色,安排全村改用心声符交流。日常交谈以手势配合简谱式符号完成,孩童游戏皆用无词旋律进行。巡查使数日无所获,只得悻悻离去。临行前,为首官员冷笑警告:“有些声音,迟早会被听见。”
十月初一,寒露。沈知白收到一封匿名信,字迹潦草,纸张粗糙:
>“大人,我是清音营厨役。昨夜送饭至地下学堂,见三十幼童排坐一室,额贴银箔,头戴环状器物,口中被迫重复单音节。有人昏厥,有人流泪,无人敢停。教师言:‘练成纯净之耳,方可聆听圣谕。’求您救救这些孩子,他们还不懂什么叫‘被听见’。”
信末附一张炭笔草图,描绘室内布局与设备位置。
沈知白彻夜未眠。次日清晨,他召集所有能吹埙、奏笛、击磬的寻声者,宣布一项计划:“我们要送一首歌进地底。”
这不是普通的音乐行动。他们要利用共听之流的传导特性,将一段特定频率组合的乐曲,通过桃树、菌丝网络、地下暗流层层放大,最终穿透岩层,抵达清音营所在方位。这首曲子不含歌词,却嵌入了百名普通人真实心跳节奏的叠加波形??那是最原始、最无法伪造的生命之声。
准备工作持续二十日。期间,桃树释放出大量孢子,随风飘散至周边村落。凡是吸入者,短期内会出现短暂幻听,听到亲人的呼唤或童年的笑声,但无不感到内心安宁。乐师们称其为“种音”。
十一月十七,大雪封山前夜。所有人齐聚无声堂,围绕中央火盆席地而坐。沈知白手持祖传陶埙,深吸一口气,吹出第一个音。
那是《归去辞》的起始调,十年未曾完整演奏。
音波荡开,桃树率先响应,枝叶轻摆,菌丝glowingfaintlybeneaththesnow。紧接着,远处几户人家的窗棂微微震颤,屋内悬挂的铜铃无风自动。百里之外,一位正在抄写经文的老尼忽然停笔,泪水夺眶而出??她听见了亡徒临终前未能说完的告解。
而在西北某处深山地底,三十名幼童同时抬头,眼中闪过一丝清明。他们挣脱束缚,齐声哼唱起一支从未学过的旋律,正是那晚桃树传递的和声。监控屏幕瞬间爆红,系统瘫痪,警报凄厉长鸣。
三天后,消息传来:清音营临时关闭,负责人“因健康原因”被调离。三十名儿童被转移至普通学堂,官方宣称“试点调整”。
沈知白听罢,只是点头,转身走进书房,取出尘封已久的《静语考》笔记,在最后一页写下结语:
>“静语非禁声,乃还声于民。听非窃取,乃共情之桥。毁塔易,毁欲难;立堂易,立信难。唯愿后人记得:每一颗愿意倾听的心,都是不可征服的城池。”
腊月初八,佛成道日。阿音煮了一锅腊八粥,特意多放了一勺红糖。
“今年多加两个。”她说。
“给谁?”
“给还没找到路的人,和已经出发的人。”
沈知白笑了。他端碗走到院中,将一勺热粥轻轻洒向桃树根部。
树身微颤,一片叶子悄然脱落,打着旋儿落在他脚边。叶脉清晰如刻,竟天然形成一行小字:
>“我在听。”
他仰头望天,雪已停歇,星河璀璨。
远处,又有一个孩子清亮地喊了一声:“爹??我看见星星啦!”
那声音划破夜空,没有禁忌,没有恐惧,只有纯粹的欢喜。
他知道,这场漫长的沉默之战,终于迎来了第一缕真正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