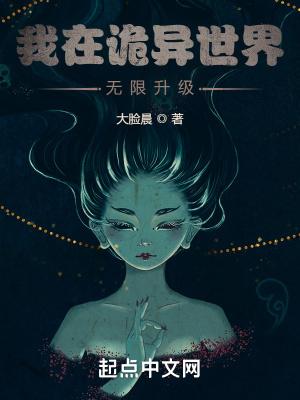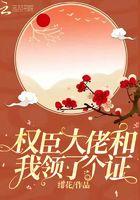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装傻三年:从状元郎到异姓王 > 第六百八十章 沈浩马上不是王爷了(第1页)
第六百八十章 沈浩马上不是王爷了(第1页)
海公公有心要劝阻,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说实在,他心里也快要气死了。
刚才他在朝堂上听到那些皇室宗亲诋毁沈王爷的话,他都差点忍不住要骂人。
那些说的都是人话么。
大京面对如此多的天灾,是谁解决的?
后宫和皇室的吃穿用度的银两是谁帮忙赚的?
打压世家,让皇室地位提升,是谁完成的?
到现在那些皇室宗亲就搬出祖宗礼法出来。
还各种言语上的侮辱。
沈王爷其实这些无能之人能侮辱的。
要不是郑国公哐哐几拳锤翻了几个嘴臭的,。。。。。。
沈知白将那片落叶轻轻拾起,指尖抚过叶脉间天然生成的文字,仿佛触到了大地深处缓缓跳动的脉搏。他没有说话,只是将叶子夹进《听见录》的最后一页,合上书册,如同封存一段尚未完全展开的命运。
阿音端着粥碗站在门口,望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沉默了三年的男人,正一点点从壳中剥离出来。她记得初见时,他是京城传颂的状元郎,眉目清朗,言辞锋利,却在一夜之间疯癫装傻,随她回到这偏僻山村。三年来,他不争不辩,不怒不语,像一株被雷劈过的老树,枯枝垂地,无人知其根系仍在暗处蔓延。而今,桃树开口,无声堂鸣响,清音营崩解??她终于明白,那些沉默不是退让,而是蓄势。
“你还记得当年在贡院外,我说过什么吗?”她轻声问。
沈知白转身,眸光微动:“你说,声音是有颜色的。”
“是。”她点头,“你说不信。可现在,你听的已不只是声音,而是心的颜色。”
他低笑一声,将碗递还给她:“那你告诉我,今晚的星河是什么色?”
“银白里透着暖红,”她说,“像一首刚醒来的心声符。”
他们并肩立于院中,雪后空气清冽如洗,远处群山覆着薄霜,宛如静卧的巨兽脊背。桃树静静伫立,枝干虬结如古篆,树皮上的裂纹自那一夜点睛之后便再未消去,反而日渐清晰,形似门户微启,似有某种存在正从中窥视人间。
次日清晨,村中孩童照例聚集晒谷场练习心声符。竹笛、陶埙、骨哨此起彼伏,旋律杂而不乱,皆依循一种隐秘的共振规律。有个七岁男孩用芦管吹出一段极短的音列,竟引得屋顶瓦片微微震颤,邻家鸡群齐齐打鸣,节奏竟与之呼应。孩子们惊叫着围拢过去,阿音闻声赶来,凝神细听后脸色骤变。
“这不是我们教的。”她低声说。
那音列古怪异常,前两拍平稳,第三拍突兀拔高,第四拍又骤然下沉,形成一个近乎撕裂的波形。它不像情绪表达,倒像是……信号。
她立刻去找沈知白。他在书房整理寻声者送来的各地密报:北境戍卒集体失聪三日,复原后声称“听见了长城哭”;江南某书院夜间传出千人齐诵《礼运大同篇》,官府派兵围捕,却发现讲堂空无一人;更诡异的是,敦煌废墟附近出现一片野生桃林,每棵树下都有乳白色菌丝交织成网,牧民称夜晚经过会听见自己五年前说过的话。
“这段音列,”阿音把芦管递给他,“它触发了菌丝反应。”
沈知白接过芦管,闭目吹奏一遍。刹那间,院中桃树叶片齐齐一颤,地下传来细微嗡鸣,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土壤中苏醒。他猛然睁眼:“这是共听残码。”
“残码?”
“第九书失落之前的原始编码片段。”他语气沉重,“原本只有持有钥匙者才能激活,但现在……有人在模仿它。”
两人对视一眼,皆觉寒意袭身。若真有人掌握了共听之流的部分机制,并试图逆向重构第九书之力,那不仅意味着静语塔计划并未终结,反而可能以更隐蔽、更危险的方式重生。
当夜,沈知白独自登上村后断崖。此处地势最高,可俯瞰整个山村与远方山谷。他取出一枚铜铃,铃身刻满细密纹路,乃祖传之物,据说是百年前静语塔建成之初,由首任守塔人所赠。传说此铃能引动“地听”,即大地本身的记忆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