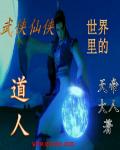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天赋异禀的少女之无相神宗 > 第535斜月山庄二百五十(第2页)
第535斜月山庄二百五十(第2页)
第七日夜里,异变陡生。
原本应在子时敲响的铜钟,竟提前一刻自鸣!钟声滚滚而出,如铁流倾泻,直扑全城。百姓惊恐闭户,捂耳跪地。可就在此时,地面开始轻微震动??先是井水泛起同心圆波纹,继而屋檐冰凌齐齐断裂,坠地之声竟形成一段奇异节奏。
紧接着,所有埋藏的铜铃同时响应,嗡鸣不止。那声音起初细弱如蚊蚋,随后层层叠加,竟与钟声形成对抗之势。更惊人的是,街头巷尾那些曾被涂鸦覆盖的墙壁,竟因震动显现出隐藏图案:一只手语写着“我们受够了”,一幅炭笔画描绘众人合力推倒钟楼,还有一行用指甲刻出的小字:“让耳朵休息吧。”
官府大惊,派兵搜捕“妖人”。但在抓捕过程中,士兵们发现一个诡异现象:每当他们靠近某个区域,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模仿当地居民的习惯动作??守寡妇人低头搓绳的姿态、孩童跳房子的步伐、甚至醉汉踉跄的节奏。他们的肌肉仿佛被无形之力牵引,成了他人生活的复制品。
恐惧蔓延。将军下令焚毁所有可疑器物,包括陶罐、铃铛、竹笛。火光冲天之际,桑娘站上废墟高台,打开陶丸,将其置于风中。
刹那间,火焰的噼啪声、人群的哭喊声、砖石倒塌的闷响,全被吸入陶丸之中。而后,一股柔和的声波扩散开来,带着海浪轻拍、树叶摩挲、婴儿初啼的混合韵律。听到这声音的人,无论军民,全都停下动作,眼中浮现久违的安宁。
“这不是魔法。”桑娘朗声道,“这是你们本来就会的语言??用身体记住的语言,用心跳传递的语言。朝廷可以禁止你们开口,却无法阻止大地替你们呐喊!”
话音未落,整座城市的地下水脉突然共振,发出低频轰鸣。那声音穿透地层,直抵钟楼根基。千年铜钟剧烈摇晃,最终“咔嚓”一声,悬梁断裂,巨钟坠地,裂为七块。
百姓怔立原地,继而爆发出无声的欢呼??他们张着嘴,却已忘记如何尖叫,只能用力拥抱、跳跃、拍打胸膛。那一刻,整个鸣阳城变成了一件巨大的乐器,演奏着人类最原始的自由之歌。
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皇帝召集群臣议策,有人主张剿灭“邪教”,有人建议收编“声术”为御用。唯有新任静听院主事柳文昭跪奏曰:“昔日纳兰歆教人听无声之声,今阿禾传弟子唤醒沉睡之心。此非叛乱,乃文明之进阶。若继续以声压民,恐天下皆成聋哑之邦。”
皇帝沉吟良久,终下诏:废除鸣阳铜钟制,赦免所有“心聋”罪囚,并命各地重建静听院分支,专司民间非言语诉求采集。同时,敕令将《听律?心声章》镌刻于太学碑林,供万代观瞻。
而此时的阿禾,正坐在海边,看着一轮红日跃出海面。她手中握着一片新拾的贝壳,壳内纹理宛若音波流转。忽然,脚底传来细微震动??不是海浪,也不是地震,而是一种熟悉的节奏,从遥远北方传来,穿越山川河流,清晰可辨。
那是桑娘她们设计的暗号:三短两长两短,意为“我们做到了”。
她笑了,将贝壳轻轻放回沙中。不久之后,潮水会把它带走,送往另一片海岸,或许会被某个孩子捡起,好奇倾听其中回响。
多年过去,阿禾寿终正寝。临终前,她召集岛上居民,嘱咐死后不必立碑,只需将她葬于当年学堂旧址之下。众人遵命,掘土时却意外发现一具早已风化的木箱,内藏数百枚微型竹哨,每支皆刻有一地名:西域、南疆、东海、北漠……
自此,每年清明,岛上孩童都会取一支竹哨吹奏。奇怪的是,不同地方吹出的调子竟各不相同,仿佛那些地名本身就有声音记忆。更奇妙的是,每当某地发生重大冤屈或灾难,相应名字的竹哨便会无故湿润,即便晴空万里。
人们渐渐相信,阿禾虽逝,但她把整个天地变成了乐器,把所有受苦者的沉默编织成了新的经文。
又不知几世轮回,某位年轻学者在整理古籍时,偶然翻到一页残卷,上面写着一段从未收录的文字:
>**真正的言语,始于无法发声的喉咙;
>最高的智慧,藏于愿意俯身倾听的双膝。
>不要问谁有权说话,而要问谁能听见。
>因为每一个试图被理解的灵魂,都是神的化身。**
他凝视良久,忽然觉得胸口发热。推开窗,只见庭院梧桐叶落纷纷,每一片落地的角度,竟恰好拼出两个字:
**听见**。
风过处,万籁俱寂,却又似有千言万语,在光与影的缝隙里轻轻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