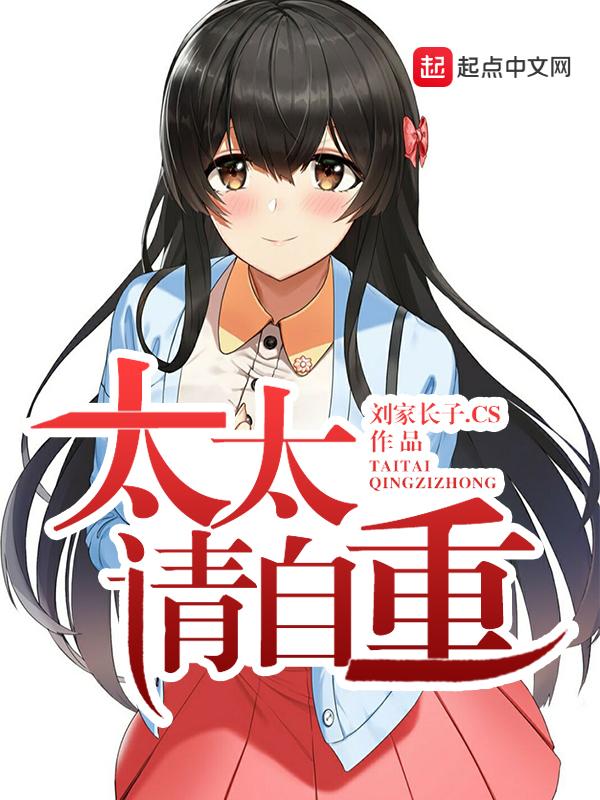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蜀汉之庄稼汉 > 第1459章 为敌谋划(第2页)
第1459章 为敌谋划(第2页)
队伍最前方,一个瘦削少年挥锄不止,汗水浸透麻衣。正是陈禾。三个月来,他每日最早起身,最晚歇息,不仅完成自身劳役,还主动帮体弱者代工。更难得的是,他利用夜间自学识字,如今已能通读《论语》前五篇,并在营地办起“夜课”,召集同伴共学。
这一日,监工送来一批新书??冯大司马亲授的《耕战策》抄本。书中提出:“边疆之固,不在长城高垒,而在每户人家门前有粮仓、院中有武备。百姓既是农夫,亦为战士,敌来则战,敌去则耕,方能长久守土。”
陈禾捧书彻夜研读,次日清晨便召集众人宣讲:“书中说,我们不是罪人,而是先锋!将来这片土地上长出的每一粒麦子,都是对过去的赎罪,也是对未来的承诺。我们要在这里建村、娶妻、生子,把陇西变成第二个青州!”
有人质疑:“真会有女人愿意嫁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陈禾朗声道:“只要你肯干,朝廷就会给你分房、分地、分牛。而且听说,明年就要从关中选派三百名未婚女子前来‘婚配屯边’,优先配给表现优异者!”
众人大哗,随即爆发出哄笑与鼓掌。压抑已久的希望,如野草般破土而出。
就在士气高涨之际,远方烟尘骤起。一队骑兵飞驰而来,为首者乃冯大司马亲卫队长赵广。他翻身下马,高声宣读诏令:
>“奉天子诏:陇西屯垦成效卓著,特赐名‘新稷乡’;赐陈禾‘忠勤楷模’称号,授九品文吏职,免其余罪;全团每人赏绢二匹、盐十斤,家属另得抚恤米五石。另,随信附来三百封家书,系长安流民营亲眷所寄,现已逐一核验,确保无诈。”
士兵们列队领取家书,有人颤抖着拆开,读着读着便嚎啕大哭。一封来自母亲:“儿啊,娘听说你在边地开荒,日日为你烧香。村里新开了学堂,你弟已入学,先生说他聪明得很……盼你保重身体,勿忧家中。”
陈禾收到的是一封陌生笔迹的信。展开一看,竟是羊祜亲笔:
>“陈禾君足下:
>自那日见你扑跪台前,我便知你非池中物。你以‘禾’为名,实乃天意。昔年我困于私情,误信谗言,致百姓流血,悔恨至今。今观你奋发向学,教化同侪,方悟大道所在。
>愿君常思‘一茎新芽可覆原野’之理,持正不阿,为民立命。他日若见我于南山书院窗外,请代我看看那片你亲手种下的麦田??它比我一生所著文章,更接近真理。”
陈禾读罢,久久伫立风中,手中信纸猎猎作响,如同招展的旗帜。
***
七月十五,中元节。长安城内外设百座祭坛,超度亡魂。冯大司马亲赴?县东营旧址,主持“流民英灵共祭大典”。三百余名死难者姓名被刻于石碑,置于纪念馆侧,供人凭吊。
仪式上,他亲自点燃第一炷香,然后取过话筒(此为工匠仿西域喇叭形制所造,可放大声音),面向万千民众说道:
“今天我们祭的,不只是死去的人,更是那些差点迷失的灵魂。他们曾被骗,曾犯错,但终究没有彻底堕落。他们在最后一刻选择了跪下,而不是举起屠刀。这份良知未泯,值得尊重。”
他又宣布:自即日起,每年七月十五定为“省愆日”(反省之日),全国休市一日,各级官府须召开“纳谏会”,听取百姓批评建议;同时设立“直言奖”,凡提出有效治国建议者,不论出身,均可获赏并录入人才库。
当晚,冯府家宴。冯大司马罕见地饮了一杯酒,望着庭中槐树沉吟不语。王?坐在对面,轻声道:“君侯可知,最近民间已有传言,称您为‘庄稼汉宰相’?”
冯大司马一笑:“庄稼汉有何不好?天下万事,终归要落在一粒种子上。种得好,五谷丰登;种不好,饿殍遍野。我不求青史留名,只愿十年之后,有人指着麦田说:‘这儿曾是一片焦土,是冯某人带着一群苦命人,把它变成了粮仓。’”
王?叹道:“可您知道最难的是什么吗?不是开荒,不是打仗,而是让人心重新相信??相信官府不会骗人,相信努力会有回报,相信明天真的会比今天好。”
“所以我才坚持写那封《告北人流民书》,办那所妇学,开那条灌溉渠。”冯大司马缓缓道,“制度是骨架,人心才是血肉。没有血肉的国家,不过是行尸走肉。”
话音未落,门外传来急报:吴国使者抵达长安,请求紧急觐见天子,带来孙权亲笔国书。
冯大司马眼神一凛:“终于来了。”
次日朝会上,吴使当廷宣读文书,言辞激烈,指责季汉“纵容流民滋事,勾结魏国细作,破坏江东安定”,并要求立即遣返所有北人流民,否则将“断绝商路,陈兵江上”。
群臣哗然,主战派纷纷请缨出征。
冯大司马却起身奏道:“臣请暂缓回应。不如先请吴使前往?县流民营参观三日,亲眼看看我们的学校、作坊、医院、坟场。若他仍执意污蔑,请陛下准许我发布《泣诉录》全文,并向天下昭告:谁在压迫百姓,谁在拯救苍生,自有公论。”
皇帝允诺。
七日后,吴使归国,带回的不仅是流民营实景绘图,还有一封由百名北人流民联署的公开信,题为《我们在季汉吃得饱》。信中详述每日餐食、工钱数额、子女教育、医疗保障,末尾写道:
>“我们不是不想回家,但我们已经找到了新的家。这里没有人半夜抓壮丁,没有官吏抢粮杀人,孩子上学不要钱,生病有大夫看。若孙权真仁慈,请让我们自由选择去留。若他强迫驱赶,请问:是他爱我们,还是爱战争?”
此信后来传至建业,引发士林震动。有江东儒生私下传抄,题签曰:“此乃庶民之声,胜千军万马。”
而远在陇西的陈禾,此时正带领新民团完成第一条干渠合龙。渠成之日,清水奔涌而入荒田,众人欢呼跳跃。他在渠首立下一块木牌,上书四个大字:
**“活路在此。”**
风吹麦浪,大地无言。但在千万双眼睛里,在无数正在发芽的种子中,一个新的时代,已然破土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