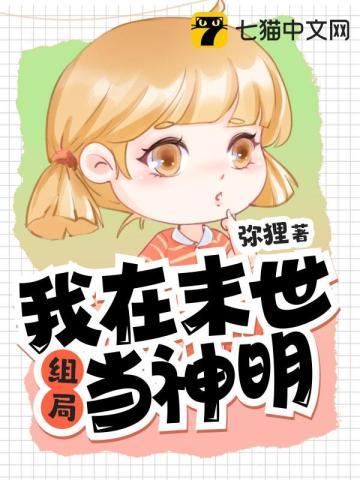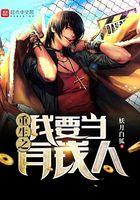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秦人的悠闲生活 > 第三百五十四章 黄老之书(第1页)
第三百五十四章 黄老之书(第1页)
大雪几乎要淹没了咸阳城,起初寒冬来得还算迟缓,可一到冬至,大雪就突如其来。
过了冬至新年,扶苏已是在位的第八年了。
大雪落在章台宫的宫殿上,扶苏看着从辽东送来的奏报,屠雎已到了辽东,并且还。。。
雪融之后,贺兰山北麓的泥土开始松动。春意尚未真正降临,但天地间已有了变化的气息。学堂前那棵槐树抽出了嫩芽,细弱却倔强,在风中微微颤动,仿佛回应着孩子们每日清晨诵读的声音。赵佗站在营门口,望着那抹新绿,心中竟生出一种久违的安宁。
他手中握着一封由长安转来的密信,是丞相李斯亲笔所书,字迹刚劲如刀刻:“陛下观贺兰教化之成效,甚慰。然胡地难驯,非一策可定。今令尔等试行‘归心三法’:其一,设‘亲子堂’,许匈奴父母入营探子,以情动之;其二,立‘耕读田’,令孩童与士卒共耕,知稼穑之艰;其三,开‘辩理会’,每月集将士、夫子、孩童及来归之胡人,共议是非,明律义。”
赵佗读罢,久久不语。他知道,这不仅是政令,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尝试??用人心去融化仇恨,用日常去消解敌意。若成,则边疆百年无忧;若败,则前功尽弃,反为天下笑柄。
他召来夫子荆与靳勇议事。靳勇听完眉头紧锁:“让匈奴人进营?万一他们趁机劫掠、刺杀主将,如何防备?”
夫子荆却抚须轻笑:“将军所虑固然有理,但若一味闭门自守,岂非正中仇恨下怀?亲子相见,乃人伦至情。我们不让见,便是断其亲情;我们主动邀见,便是布以仁信。纵有奸谋,亦可用礼法规制之。”
赵佗点头:“便依此议。但须严加防范,每名来者皆须卸兵刃,由两名秦军escort入营,不得自由走动。且首次只允五人入内,待观其行止再作扩增。”
三日后,第一批探视者抵达。除呼延彻外,另有四位匈奴部族首领或家长,皆骑瘦马而来,神色戒备。他们被引入营地中央特设的“亲子堂”??原是一间废弃粮仓改建而成,屋内铺草席,设矮案,墙上挂着《孝经》节选与一幅手绘地图,标明秦郡与草原诸部位置,题曰:“同天共土”。
当库尔班跑进屋子扑向父亲时,呼延彻眼眶骤然泛红。他蹲下身,双手捧起儿子的脸,反复确认是否受过苦楚。见孩子面色红润,衣履整洁,还识得几个字,竟一时哽咽无言。
其余几位家长也陆续与子女相见。有的孩子久别亲父,怯怯不敢近前;有的则扑入怀中放声大哭。一名年仅六岁的女孩拉着母亲的手不肯松开,反复说着:“娘,我学会写‘安’字了,夫子说,心里平安才是真平安。”
夫子荆端坐一旁,未发一言,只命人送上热汤与粗饼。待众人情绪稍定,他才缓缓开口:“诸位远道而来,可知我们为何肯放你们进来?”
无人应答。
“因为我们不愿做仇人。”他说,“你们的孩子在这里吃饭、读书、习礼,并非为了羞辱你们的血脉,而是为了让你们的子孙不必再提刀杀人,也不必再被人杀死。你们可愿看看他们学了什么?”
随即,孩子们依次上台展示所学。有人背诵《千字文》,有人讲解“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更有三人合演一段“乡饮酒礼”的简化仪式,虽动作生涩,却庄重认真。最后,库尔班取出一张粗糙纸张,上面是他亲手抄写的《医方十八症》中一段:“凡伤寒发热者,宜避风寒,饮热水,卧暖处……”
“这是我记下来的。”他抬头对父亲说,“上次阿古斯哥哥高烧不退,我就照着这个给他盖被子、喂姜汤,第二天就好了。夫子说我将来可以当医助。”
呼延彻盯着那张纸,良久不动。终于,他低声问:“你……还记得草原上的歌吗?”
库尔班点点头,轻声哼起一支匈奴古调,歌声清越,带着北方特有的苍凉。唱完后,他又补充道:“我也学会了秦地的《鹿鸣》,要一起唱吗?”
父子二人在众人注视下,竟真的合唱起来。一曲终了,满室寂静。连最警惕的秦军哨卫也都低下了头。
当晚,五位匈奴家长皆愿留下宿夜。赵佗破例允许他们在亲子堂过夜,仅派十名精锐在外围值守。翌日清晨,呼延彻主动找到赵佗,递上一把小匕首??那是他随身携带多年的贴身之物。
“我把它留在这里。”他说,“不是投降,是信任。若我儿真能成为你说的那种人,那草原或许真该变一变了。”
赵佗郑重接过,命人将其悬于学堂正堂梁上,题曰:“信始之物”。
自此,“亲子堂”每月开放一次,前来探视的匈奴家庭渐多。起初尚有争执怒骂者,指责孩子“忘了祖宗语言”,甚至动手撕毁课本。但每当夫子荆请孩子当场背诵一段律法、演示一次包扎、或是讲述一则农事常识后,多数家长都会沉默离去。有些人临走前,还会悄悄塞给孩子一块干肉或一件皮袄。
与此同时,“耕读田”也在春耕时节正式开垦。百亩荒地被划分为若干小块,每两名孩童配一名老兵共同耕种。种子来自关中运来的粟、麦与豆类,工具则是军中铁犁与木耙。夫子荆亲自讲授《吕氏春秋?任地篇》中的耕作之道,强调“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
起初,匈奴孩童不解农事,常将种子撒得太密,或浇水过量。老兵们起初嗤笑,称其“马背上的崽子怎懂泥土滋味”,但随着禾苗破土而出,绿意蔓延,他们也不由得投入其中。更有老兵自愿教授如何修渠引水、如何堆肥防虫,甚至编了一套口诀教孩子们记忆节气:“惊蛰响雷麦起身,清明下种莫迟延。”
到了五月,耕读田里麦浪翻滚,金穗低垂。收获当日,全营举行“尝新礼”。孩子们亲手收割、脱粒、磨粉、蒸馍,然后捧着第一笼热腾腾的麦饭献给夫子荆与赵佗。
“此非仅食粮之获,”夫子荆执碗而立,“乃是知行合一之始。今日你们手中之馍,既出自土地,也出自学问。往后无论身处何方,只要记得这一口滋味,便不会忘记何为生计,何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