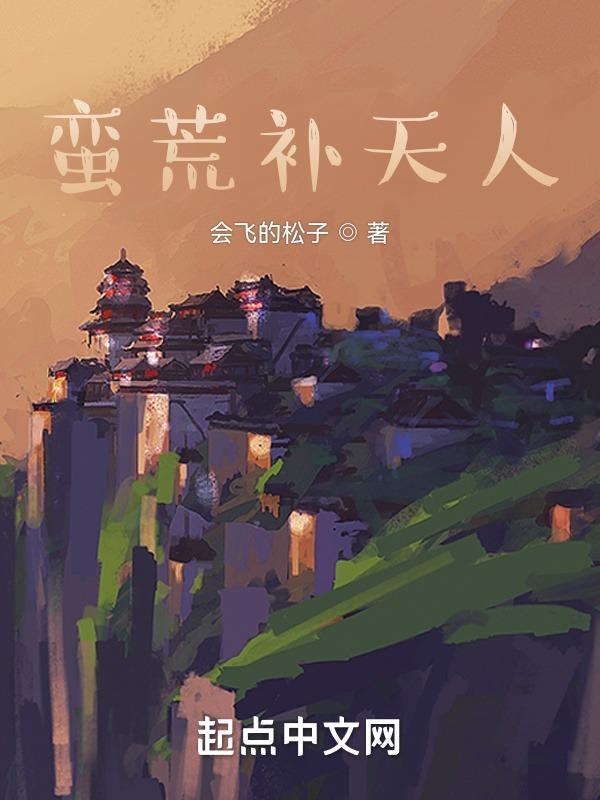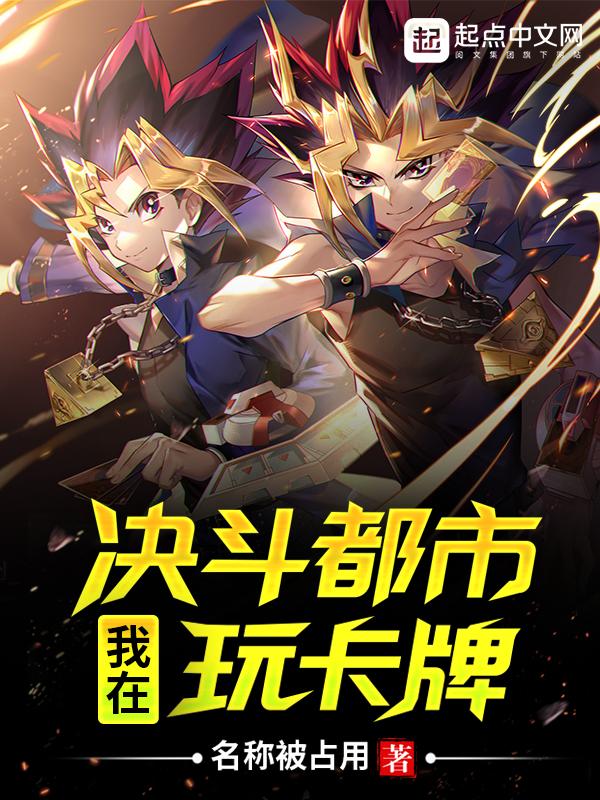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重启人生 > 0516你能想象微信搭载支付宝吗(第2页)
0516你能想象微信搭载支付宝吗(第2页)
许风吟沉默良久,终于明白:哭嫁歌之所以能疗愈女性,并非因其形式神圣,而是因为它允许一个人公开地、合法地、被尊重地表达悲伤。而在这些留守儿童的世界里,连“想爸爸”都成了一种羞耻。
第三天,“梦境剧场”正式开启。孩子们围坐一圈,有人捏黏土,有人画画,有人静静听着别人讲述。轮到阿?时,她依旧不说话,却捧出一张新画:画面是夜晚的院子,天上挂着半轮月亮,树下摆着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两副碗筷,一碗米饭,一碗空着。
张老师轻声问:“另一碗,是留给谁的?”
阿?低头抠手指,许久,才用细若游丝的声音说:“爸爸……说今年回来过年。我没信。可我还是每天洗碗,摆好位置。”
全场静默。许风吟鼻子发酸。他知道,这不是谎言,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希望??她不敢相信,却又不愿彻底放弃。
他取出录音笔,放在她手边:“要不要录一句话?不用给他听,就当是告诉今晚的月亮。”
阿?摇头,却又迟迟不走。最后,她拿起蜡笔,在画纸背面写下一行字:
>“爸爸,今天我考了第一名。
>老师表扬我了。
>你要是看见,会不会笑一下?”
许风吟将这张画扫描存档,在《回声档案》第七十六页写道:
>**编号03,姓名:阿?。
>八岁,苗族,雷山小学二年级。
>母亲因病去世三年,父亲长期外出务工,年均归家不足十五日。
>自幼表现出情感隔离倾向,拒绝提及父亲,回避家庭话题。
>近期通过绘画暴露深层依恋需求,表现为“等待仪式化”行为(每日摆碗筷)。
>昨夜于哭嫁歌声中首次触发潜意识语音,表达被忽视感与渴望认可。
>今日以文字间接传递成就信息,标志封闭系统出现主动输出迹象。
>此非求和,而是试探性的连接尝试。**
当晚,许风吟独自爬上寨后山坡。山顶有一块平石,相传是古时新娘出嫁前最后一跪之地。他坐在石上,播放阿?的录音片段,一遍遍听着那句“你要是看见,会不会笑一下”,心口像被什么攥紧。
忽然,远处传来脚步声。回头一看,竟是阿?,穿着单薄的校服,赤脚踩在露水打湿的草地上,怀里抱着那张画。
“你怎么一个人上来?”许风吟急忙起身。
女孩不答,走到石边,把画轻轻放在地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小的竹笛??那是村里老人常给孩子做的玩具,只能吹出几个简单音符。
她试着吹了一下,声音短促而颤抖。接着,她又吹了一遍,这次拉长了些,像是在模仿某种呼唤。
“这是……你爸爸教你的?”许风吟轻声问。
阿?点头,眼里泛起泪光:“他说,只要我在山上吹笛子,他就能听见。可我吹了好多次,他都没回来。”
许风吟蹲下身,握住她的手:“你知道吗?有时候,亲人听不见,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而是因为距离太远,声音传不到。但你吹的每一口气,都在提醒你自己??你还爱他,你还记得他。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