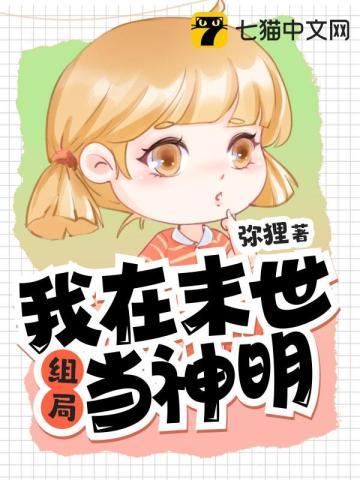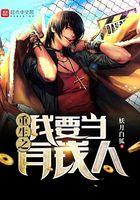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大唐协律郎 > 0534 神仙打架小鬼遭殃(第2页)
0534 神仙打架小鬼遭殃(第2页)
张岱心头一震,低头道:“臣惶恐。”
玄宗站起身,缓步走下亭阶,负手望向湖面:“朕登基以来,励精图治,开元盛世,百姓安居。然太平日久,官吏懈怠,豪强兼并,隐户日增。若再不整顿,十年之后,国库空虚,边防无力,社稷危矣。”
他顿了顿,回头看着张岱:“姜行威所奏,虽手段激烈,却是救时良策。裴稹融所虑,虽出于仁心,却有因循守旧之弊。朕思之再三,决意采纳姜相公之议,推行括户新政。”
张岱心中大震,连忙叩首:“陛下英明!此举实乃利国利民之策!”
玄宗摆手:“但朕也知道,此政一出,必遭权贵反对,地方阻挠。若无铁腕之人推行,终将半途而废。故朕欲命姜行威总领此事,另设‘括户使’专司其职,统筹全国清查。”
说到这里,玄宗目光炯炯地盯着张岱:“而这个人选,朕想交给你。”
“臣?!”张岱愕然抬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正是你。”玄宗语气坚定,“你年轻,无派系牵绊,又有监察之责,更难得的是,今日你敢于执法如山,不畏权贵。这样的人,才堪当此任。”
姜行威在一旁闻言,眼中闪过欣慰之色,却并未言语。裴稹融则眉头紧锁,显然对此安排极为不满,但面对天子圣断,也只能默然接受。
张岱心跳如鼓,脑海中电光石火般闪过无数念头:这是机遇,也是危机。一旦接手括户使,必将触动无数豪族利益,树敌遍天下。可若推辞,便是辜负圣恩,更失姜相公栽培之义。
他深吸一口气,伏地道:“臣才疏学浅,恐难胜任。然既蒙陛下信任,纵粉身碎骨,亦当竭尽全力,不负所托!”
“好!”玄宗大笑,“有此志气,何愁大事不成!”
当即命内侍取来敕书,正式任命张岱为“括户使”,赐紫服银鱼袋,秩比正五品上,可直达天听,巡察诸道,纠察不法。
仪式完毕,玄宗又叮嘱道:“此事关系重大,切记稳中求进,不可操之过急。若有疑难,随时奏报。朕,是你最大的靠山。”
张岱含泪叩首:“臣誓死效忠陛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退出沉香亭时,夕阳已斜照宫墙。张岱手捧敕书,脚步沉重却又坚定。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已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年轻御史,而是卷入帝国权力漩涡中心的关键人物。
刚走出宫门,便见贺知章、王翰等人迎上前来,脸上写满震惊与激动。
“八郎!你竟得了括户使之任?”贺知章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声音都在发抖,“这可是震动朝野的大事啊!”
王翰亦惊叹:“圣上如此器重于你,足见你已入天子心腹之列!”
张岱苦笑:“此非荣耀,实乃重担。从此以后,我不只是姜相公门生,更是新政先锋。那些被触动利益的人,不会放过我。”
正说着,忽听远处一阵喧哗。只见宇文兄弟率众而来,一个个面色阴沉。宇文宽更是直接上前,冷笑道:“恭喜张大人高升啊!不知日后查抄我家田产时,能否念及旧情,网开一面?”
张岱冷冷看他一眼:“若有隐匿不报、侵占民田者,无论亲疏,一律依法处置。宇文郎若问心无愧,又何必担忧?”
宇文宽脸色铁青,还想再说,却被身旁兄长拉住。他们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已经不再是任人拿捏的小角色了。
夜幕降临,兴庆宫恢复了宁静。然而整个长安城,却因今日之事而暗流涌动。
东市某宅院内,裴稹融正与心腹密议。
“圣上偏袒姜党至此,实在令人寒心!”裴稹融拍案而起,“那张岱不过乳臭未干,竟委以如此重任,简直是儿戏国政!”
幕僚低声劝道:“相公息怒。眼下之势,不可硬抗。不如暂退一步,待其新政推行不利之时,再寻机反击。”
裴稹融冷哼:“新政?哼,括户之举看似利国,实则扰民。地方官吏趁机勒索,百姓苦不堪言。只需一年半载,必生民怨。届时,看玄宗如何收场!”
与此同时,在崇仁坊一处幽静别院中,姜行威正在灯下书写文书。听到下人禀报张岱已被任命为括户使,他放下笔,仰头长叹:“终于开始了……孩子,这条路不好走,但我相信你能走下去。”
而在南郊凤栖原下的逍遥园里,宇文宽独自立于荒园之中,望着残垣断壁,眼神狠戾:“张岱,你夺我园墅,今日又得高位……这笔账,咱们慢慢算。”
长安的夜风拂过城墙,带着春末夏初的燥热。一场关乎大唐命运的改革风暴,正悄然酝酿。而张岱,已然站在了风暴眼的最前端。
他知道,未来的路充满荆棘,或许还有杀机潜伏。但他更清楚,若无人挺身而出,这个帝国终将在安逸中腐朽。
所以他选择前行。
哪怕孤身一人,也要点燃那一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