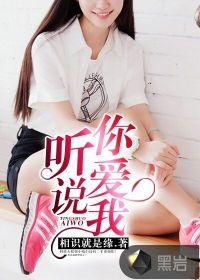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二婚嫁京圈大佬,渣前夫疯了 > 第1550章 一起去看外婆(第2页)
第1550章 一起去看外婆(第2页)
>
>**但您错了。她不是表演,她在生活。她的每一次发声,都不是为了取悦谁,而是向命运宣告:我不认输。**
>
>**至于‘无法复制’?我同意。因为真正的教育,本就不该是流水线产品。每个孩子都值得独一无二的投入。**
>
>**如果您愿意,请来基地看看。看看她如何教弟弟妹妹打手语,如何在雨里抱回一只受伤的鸟,如何在深夜发烧时仍坚持练习发音。**
>
>**然后您再告诉我??这是虚假希望,还是真实的生命力?**
信末附上一段视频:小满独自在录音棚练声,一句话重复了整整四十遍,直到最后一个音终于清晰。她累得趴在桌上,却又笑着抬头,对着镜头比了个“胜利”。
舆论瞬间反转。
网友纷纷留言:
“原来我们看到的轻松,背后是这样的咬牙坚持。”
“请别用冰冷的数据否定温暖的努力。”
“如果这叫表演,那我宁愿全世界都来演一次。”
更有许多听障家庭晒出孩子的照片和视频,配上一句话:“我们也在努力,哪怕慢一点。”
周维衡未再回应,但三天后,他悄悄注册了“回声行动”志愿者账号,备注写着:“想亲眼看看,什么叫生命力。”
压力尚未消散,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声音节”选址定在城郊生态公园,原计划搭建临时舞台与展览区。可就在施工第三天,环保部门突然叫停工程,理由是“未经审批占用绿地”。
项目组紧急召开会议,律师查证后发现,申请材料确实在递交过程中被人篡改,关键页码缺失,公章疑似伪造。
“有人不想让我们办成。”阿岩咬牙。
沈知远却异常冷静:“查监控,追源头。同时启动备选方案??把场地移到念安学校操场。”
众人哗然:“可那里没电源、没音响、没观众席!”
“那就造。”他说,“我们当初建基地时,什么都没有。”
于是,一场意想不到的全民共建开始了。
消息传开后,第一拨支援来自曾经受助的家庭。一位父亲开着卡车送来二十套太阳能板,说:“你们教会我儿子说话,这是我能做的。”
一位母亲带着手工社团成员连夜缝制防雨坐垫,每块背面绣着一句话:“听见,不止一种方式。”
本地高校学生自发组成运输队,扛着音箱、灯具、帐篷一趟趟往返。
最让人动容的是,一群退休教师联合捐款,购置了一批便携式震动背心??穿上它,听障观众能通过身体感受音乐节奏。
开工第七天,天空突降暴雨。工地泥泞不堪,设备进水,许多人以为活动将被迫取消。
可凌晨四点,小满却醒了。她穿上雨靴,拿起伞,默默走到院子里,开始清理积水。陈婉发现时,她已搬动了好几箱物资。
“回去睡觉。”陈婉心疼地说。
小满摇头,写下:“姐姐说过,只要人在,希望就在。”
这句话像火种,点燃了整个团队。天刚亮,三十多名志愿者冒雨赶到,有人架设防水棚,有人抢修电路,还有位老木匠亲手打造了一排弧形木椅,按声波形状排列。
第十天,阳光重现。
操场上,一座由爱与执念筑成的艺术空间拔地而起。主舞台以“耳蜗”为设计灵感,螺旋展开;四周悬挂着上千只纸鸟,每只翅膀内嵌LED灯,随音乐变色;中央地面铺设感应震动层,踩上去会泛起涟漪般的光晕。
彩排当天,小满第一次站上这个属于她的舞台。她闭上眼,把手贴在地板上,感受着后台传来的钢琴前奏??那是《她说》的新编版本,加入了童声合唱与手语舞蹈。
她忽然睁开眼,在纸上快速写下一段话,递给沈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