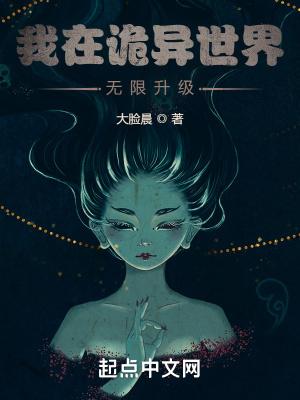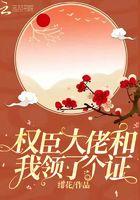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春色满棠 > 第487章 开启一个新的朝代(第2页)
第487章 开启一个新的朝代(第2页)
>昨天我听了您的课,回家就把课本翻出来,指着上面的字念给她听。她突然哭了,说她小时候也想上学,可爷爷说“丫头片子识几个字就行了”,把她送去给人做童养媳。
>
>今天早上,我发现她把我掉在地上的铅笔捡起来了,擦干净放在枕头底下。她说:“这是你念书的家伙,不能丢。”
>
>老师,我想请您帮个忙??下次讲周阿娣的故事时,能不能慢一点?我想抄下来,念给我妈听。
>
>学生田秀兰
林小禾将信折好,轻轻压在母亲日记本上。窗外,暮色渐浓,晚风拂动窗棂,带来远处溪流的声响。
第二天清晨,她带着几名高年级学生前往怒江上游考察。那里有一段尚未修复的“女子道”残段,据当地老人说,曾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女性挑粮送药的必经之路。山路陡峭,一侧悬崖深不见底,另一侧岩壁风化严重,碎石频落。
走到半途,天空骤然变色,乌云压顶,暴雨倾盆而下。学生们慌乱躲避,有人脚下一滑,险些坠崖,幸被陈砚一把拽住。众人退至一处岩洞避雨,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冷得直打哆嗦。
“怎么办?”一个女生牙齿打着颤,“回不去了吗?”
林小禾点燃随身携带的蜡烛,火光映亮岩壁。她忽然注意到,石缝间竟刻着几行模糊字迹。她掏出笔记本和炭笔,轻轻拓印下来:
>“丙午年三月初七,李桂芳、张玉梅、王秀英三人修此路,为女童上学便。”
>
>“路难,不如命苦。宁挖十丈石,不误一日学。”
>
>“若后人至此,请替我们看看山外的模样。”
洞内一片寂静。
“她们……是谁?”有学生低声问。
“我不知道。”林小禾轻抚那些刻痕,声音微颤,“但我知道,她们和我们一样,相信一条路能改变命运。”
那一夜,他们在岩洞中度过。没有食物,只有雨水和干粮;没有床铺,只有一层薄毯垫在石地上。但没人抱怨。几个女孩围坐在一起,轮流朗读《她说?家常》中的故事,声音在空旷山洞中回荡,仿佛穿越时空的对话。
凌晨雨停,天边泛起鱼肚白。他们继续前行,终于抵达那段残道尽头。荒草掩映中,立着一块歪斜的石碑,上面依稀可见三个字:**素心亭**。
“原来……真有这个地方。”陈砚喃喃道。
林小禾走上前,拂去青苔,果然在背面发现一行小字:
>“此亭为纪念林素心老师而建。1962年春,桐木坪村民集资。”
>
>“虽未立碑于世,然心碑永存。”
她怔住了。这是第一次,她亲眼见到母亲的名字被村民郑重铭记。不是在档案馆冰冷的卷宗里,不是在批判文件的罪名列表中,而是在这荒山野岭的一块石头上,在风雨侵蚀也无法抹去的深情里。
返程途中,她默默许下一个愿:要把这段残道修复,建成“素心之道”的实景教育基地。不仅要铺路,还要在沿途设立口述史站点、女性教育纪念碑、乡村图书角。让每一步行走,都成为一次记忆的唤醒。
一个月后,项目启动会在春禾学堂召开。除了原有团队,还邀请了多位曾受林素心影响的学生代表。会议进行到一半,门口走进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在苏晓搀扶下缓缓坐下。
“我是陈雨晴的母亲。”她开口,声音沙哑却清晰,“我女儿临终前托我一定要来一趟。她说:‘你要替我去看看那个女孩,告诉她,我不是白白活过这一生。’”
全场肃然。
老人从怀中取出一只铁盒,正是当年藏教案的那个。盒盖打开,里面除了一份泛黄的手写教材外,还有一张照片??年轻的陈雨晴与林素心并肩站在桐木坪小学门前,两人笑容灿烂,身后一群小女孩蹦跳着挥手。
“素心常说,教育是种种子。”老人看着林小禾,“现在我看到了,那颗种子长成了树,还在继续撒播新的种子。”
会后,林小禾将这张照片扫描存档,并决定将其作为《春在不肯低头的脖颈》再版封面。同时,她正式向教育部提交申请,建议将“女子道”纳入全国中小学生社会实践路线,命名为“女性觉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