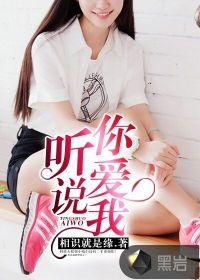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医路坦途 > 第九百零五章 办法多的很(第2页)
第九百零五章 办法多的很(第2页)
那一晚,没人提议结束。星空低垂,仿佛伸手可触。张凡仰头望着银河,耳边传来细微的抽泣与低语,像风吹过山谷的回响。他知道,有些东西正在悄然改变??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共情的萌芽;不是单向的救助,而是双向的照亮。
第三天,天气突变。乌云压顶,气温骤降。原定户外活动被迫取消,所有人转入祠堂避寒。谁也没料到,这场意外促成了最具意义的一次交流。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阿?提议,“叫‘假如我看不见’。”
规则很简单:两人一组,一人蒙眼,另一人引导其完成指定任务,如穿针、倒水、写字。起初大家嘻嘻哈哈,可当真正失去视觉后,恐慌迅速袭来。有人撞到柱子,有人打翻茶杯,更有孩子急得哭了:“我看不见了!怎么办!”
“别怕,我在。”扎西握住搭档的手,慢慢引导他摸清桌面边缘,“你看不见,但我看得见。我会告诉你每一步该怎么走。”
一个小时后,游戏结束。所有人摘下眼罩,神情迥异。一位平时最爱炫耀新款电子表的城市女孩红着眼圈说:“原来一分钟看不见就这么难……我以前嘲笑班上戴助视器的同学装模作样,现在想想,真不该。”
张凡没有点评,只是播放了一段视频??那是“记忆银行”里一段匿名上传的内容:一位渐进性失明的母亲,在视力彻底消失前,录下了女儿跳舞的画面。她反复抚摸屏幕,喃喃道:“我要记住她的裙摆是怎么转起来的。”
教室里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傍晚,暴雪来袭。电力中断,整个山寨陷入黑暗。正当众人准备点燃蜡烛时,十几盏头灯陆续亮起??是“光影伙伴”们提前准备的应急装备。更令人惊喜的是,有人拿出改装过的护目镜,连接小型电源后投射出柔和的蝴蝶光影,在墙上翩翩飞舞。
“这是我们送给你们的新年礼物,”阿?笑着说,“即使没电,光也不会熄灭。”
那一夜,孩子们挤在火塘边讲故事、唱歌、写信。张凡收到一封来自李哲的纸条:“张老师,我决定了,长大后要研究能让盲人‘看见’声音的设备。我不想再让爸爸靠摸拼图才能知道图案了。”
第四天雪停,太阳破云而出。阳光照在积雪上,折射出亿万颗细碎的星芒。全体成员徒步登上寨后山脊,举行“放蝶仪式”。每人手中都有一只手工折成的纸蝴蝶,翅膀上写着愿望或承诺。随着一声哨响,百蝶齐飞,乘风而上,宛如一场无声的祈祷。
张凡站在高处,看着那些彩色的身影融入蓝天,心中涌起难以言喻的安宁。他掏出手机,拍下这一刻,附言发送给闫晓玉:“告诉教育部,我们的反向科普课可以开始了。不是我们在教他们,是他们在唤醒我们。”
返程前一天晚上,长老邀请张凡单独谈话。老人从木匣中取出一本泛黄的手抄本,封面写着《光经》两个字。“这是我们祖先记录的草药治眼方,也有按摩手法、饮食禁忌。过去几百年,靠口耳相传,差点失传。现在你们带来了机器,但我们也有自己的智慧。能不能……把这些也录入你们的系统?”
张凡双手接过,郑重点头:“不止录入,还要标注来源、验证疗效,做成‘民族视觉遗产数据库’。这是属于全人类的知识。”
老人笑了,眼角皱纹如花瓣舒展。
归途路上,孩子们疲惫却满足。车厢内少了嬉闹,多了沉思。一个小女孩趴在窗边,看着远去的群山,忽然说:“我觉得木戛不像地图上的一个小点,它更像一颗心脏,跳得很慢,但很有力量。”
张凡望向她,微笑不语。
回到昆明当晚,他连夜起草了一份新提案:《“千灯计划”2。0版??构建城乡视觉健康共同体》。核心内容包括设立“双轨导师制”,让“光影伙伴”与城市青少年结对互学;开发“文化敏感型AI问诊模型”,融合现代医学与民族医药经验;并在全国建设十座“光之驿站”,作为流动科普站点与心理支持中心。
邮件发出后,他打开“记忆银行”后台,发现新增了三百二十八条记录。其中一条来自阿?,标题是《我想记住的十个瞬间》。第一条写着:“2024年1月18日,城里孩子教会我用微信语音发笑脸。原来快乐真的会传染。”
他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那一张张面孔:倔强的、羞涩的、灿烂的、含泪的……他们不再只是被帮助者,而是正在成长为撑起一片天的力量。
几天后,春节临近。苍北医院大厅挂起了一幅巨型剪纸作品,由各地“光影伙伴”共同创作,主题是“万家灯火”。每一盏灯下,都刻着一个孩子的名字和一句话。张凡的名字也在其中,旁边写着:“他让我们知道,黑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忘记曾经见过光。”
除夕夜,烟花升腾。张凡站在阳台上,手机忽然震动。是一条群发消息,来自“烛瞳”系统自动推送的新年寄语,署名为所有注册用户:
“亲爱的守护者:
这一年,我们测了1,036,729次视力,
走了28,453公里山路,
救回了个即将失明的眼睛,
也点亮了无数颗快要熄灭的心。
你说你是我们的光,
可你知道吗?
你也是被我们照亮的人。
新年快乐,
愿天下无盲。”
他久久凝视屏幕,直至眼角湿润。远处钟声敲响,新岁来临。
这个世界依然有太多看不清的地方。但他知道,只要还有人在坚持记录光明、传递光明、相信光明,那么总有一天,所有的黑暗都将变成光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