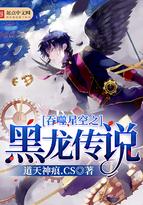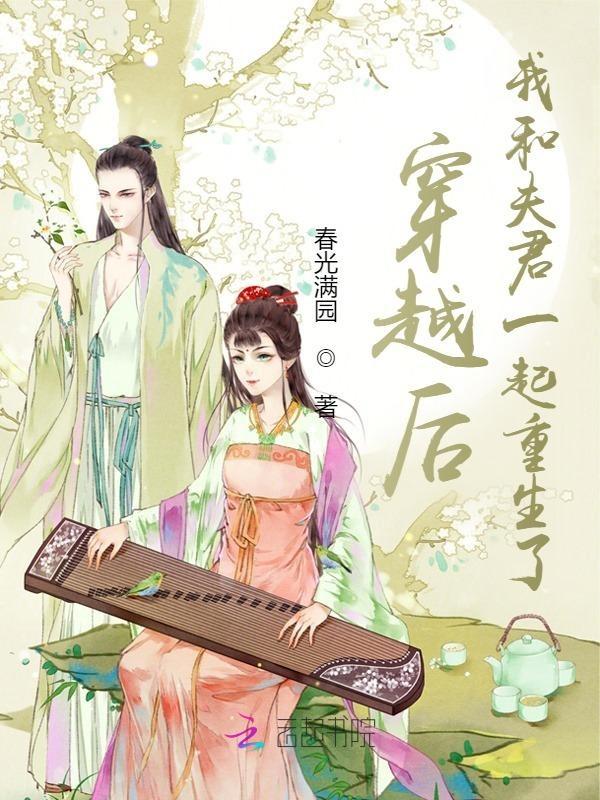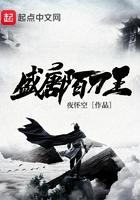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医路坦途 > 第九百零六章 甜甜的脚有救了(第1页)
第九百零六章 甜甜的脚有救了(第1页)
“退休前实职处级以上的退休干部请在十一月十五日前携带退休证书及保健卡前往茶素医院二分院干部病房注射流感疫苗,十五日后则视为主动放弃此次权利。非实职处级干部另行安排。注:实职处级为曾任地县班长,厅级室处。。。
雪融后的山道泥泞不堪,车队缓缓驶出木戛寨时,晨雾还未散尽。车轮碾过结冰的水坑,溅起一片碎银般的光。孩子们趴在窗边,望着渐渐远去的寨子,谁也没说话。那座曾被他们称作“地图上的小点”的村落,此刻像一颗嵌在群山褶皱里的星辰,微弱却执着地亮着。
李哲坐在前排,怀里抱着一只纸蝴蝶??是他昨夜悄悄折的,翅膀上用铅笔写着:“我要让声音变成画。”他没告诉任何人,但张凡看见了,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这个动作仿佛是一句无声的承诺。
回程途中,“萤火方舱”变成了移动课堂。车载AI重新连接网络后,自动同步了“记忆银行”最新数据。屏幕上跳出一条来自扎西的消息:【今天早上,我教阿?用护目镜录了一段视频。她说想看看自己唱歌的样子。】附带的短视频里,阿?站在溪边,头戴设备,一边唱《星星的颜色》,一边看着AR投影中自己的虚拟影像,笑得像个得到新玩具的孩子。
“老师,我们能不能把这套系统留下来?”一个城里女孩忽然问,“不是只给设备,是教会他们怎么用、怎么修、怎么传下去。”
张凡点头:“已经在做了。‘光之驿站’的第一站就设在木戛,半年内建成。我们会培训本地青少年成为‘光影导师’,负责维护设备、更新课程、收集病例。”
话音未落,后排传来低低的啜泣声。转头一看,是那个曾嘲笑助视器同学的女孩。她低头撕着笔记本的一角,叠成一只小小的船。“我想给我班上的小宇写封信,”她哽咽着说,“以前我觉得他戴那个眼镜很奇怪……可现在我知道,那是他在努力看见这个世界。”
车厢里静了几秒,随即有人轻声说:“我也想写。”
于是,在颠簸的山路间,十封手写信悄然诞生。有的字迹工整,有的涂改多次,内容却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对不起”、“谢谢你”和“我会记得”。张凡将这些信收好,放进随身背包最内层??他知道,这不只是孩子的忏悔或感动,而是一种认知的重塑,一种共情能力的真实生长。
抵达昆明已是傍晚。医院门口拉起了横幅:“欢迎‘光影体验团’凯旋”。闫晓玉带着几位同事等候多时,手中捧着热汤和毛毯。见到张凡下车,她快步迎上,眼里闪着光:“教育部批了你的提案!‘千灯计划’2。0正式立项,首批资金下周到账。”
张凡怔住,随即笑了。他没急着回应,而是从包里取出那本《光经》,郑重递给她:“先别谈钱的事。我们得做一件事??把这本书数字化,还要请民族医学专家参与验证每一条药方。”
闫晓玉翻开泛黄的纸页,指尖微微颤抖。一页记载着“岩蜂蜜配雪莲汁滴目,治赤眼”;另一页绘有眼部按摩穴位图,标注着傈僳语名称;更有一节讲夜间采药须避“月盲风”,需以铜铃引路。“这些……都不是现代眼科能覆盖的知识体系。”她喃喃道。
“所以才要建‘民族视觉遗产数据库’。”张凡语气坚定,“我们不能只带着技术下乡,还得学会跪下来听老人说话。科学不是唯一的真理,但它可以成为桥梁??把散落在民间的经验,接进未来的医疗网络。”
当晚,苍北医院召开紧急会议。除了院领导,还邀请了三位少数民族村医视频连线。一位来自怒江的纳西族老医生讲述了他用“松针熏目法”治疗干眼症三十年的经历;另一位藏族医师分享了高原雪盲急救中使用的“冰石冷敷术”;第三位则是木戛寨前任接生婆,她说:“我们祖辈都知道,新生儿第一眼见什么颜色,会影响他一生对光的感知。所以我们总在清晨接生,让孩子第一眼看天。”
会议室鸦雀无声。这些经验从未进入正规医学记录,却被一代代口耳相传。张凡提出建议:成立“传统视觉疗法验证小组”,由三甲医院与民族地区联合开展临床对照研究,符合条件者纳入国家中医药数据库,并开放AI训练权限。
“这意味着什么?”院长问。
“意味着未来某个孩子戴上护目镜时,系统不仅能提醒他‘当前光照不足’,还能根据他的民族体质,推荐‘苗药熏蒸+蓝光调节’的复合方案。”张凡答,“真正的个性化医疗,必须包含文化基因。”
会议结束已近午夜。张凡独自留在办公室,打开电脑开始整理《光经》扫描件。正当他逐页标注关键词时,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阿?发来的语音消息,背景有孩子们嬉闹的声音:
“张老师,告诉你个好消息!昨天晚上停电,我们用旧电池和投影模块做了个‘会飞的蝴蝶灯’,挂在祠堂梁上。今天全村小孩都跑来看,连隔壁寨子的人都来了!扎西说,这是咱们‘光之驿站’的雏形呢!”
接着是一段录音??一群孩子齐声喊:“张老师,我们等你回来!”
他闭上眼,嘴角扬起。窗外城市灯火通明,可他脑海里全是那盏摇曳在黑暗中的蝴蝶光影,温柔、倔强,像一粒不肯熄灭的星火。
第二天清晨,新生儿科传来喜讯:37床的小宝宝第二次追视成功,这次持续了六分十八秒。护士激动地说:“他居然伸手想去抓那只虚拟蝴蝶!”
张凡赶到保温箱前,正好看见屏幕上那只蝴蝶轻轻绕圈飞行。小生命躺在玻璃舱内,瞳孔随着光影移动,睫毛颤动如初醒的蝶翼。他忽然想起长老说过的话:“光母封存的不是光明本身,而是寻找光的勇气。”
那一刻,他决定启动一项新实验??将“烛瞳”系统的婴儿早期干预模块升级为“光语启蒙计划”。通过特定频率的彩色光影刺激,配合母亲录音讲述故事,帮助早产儿建立“视觉-听觉-情感”联结。首期试点选在木戛寨与昆明两家妇幼保健院同步进行。
项目申报书刚提交,又接到一个意外电话:国家盲人学校希望引入“光影伙伴”模式,让视力正常的孩子与视障学生结对学习。“我们不想再搞特殊教育隔离了,”校长说,“我们要融合,要互相照亮。”
张凡挂掉电话,走出办公楼。阳光正好洒在大厅那幅《万家灯火》剪纸上,每一盏灯都在反光。他抬头望去,发现不知何时,有人在自己名字旁边添了一行小字:“他说,每个孩子都是光源。”
春节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周,“光之驿站”建设正式启动。选址定在木戛寨小学旧址,原是一座废弃的夯土房,屋顶塌了一半,墙上爬满藤蔓。第一批物资由“萤火方舱”运抵,包括太阳能板、卫星通信终端、便携式VR教学套件和一台可打印盲文的多功能打印机。
更令人振奋的是,十名“光影伙伴”中有七人自愿报名担任首批志愿者。他们利用周末坐班车进山,一边清理废墟,一边教当地孩子组装设备。阿?学会了使用电钻,扎西能独立调试投影仪,就连普秀英也尝试用手机拍摄教学短视频,虽然镜头总是晃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