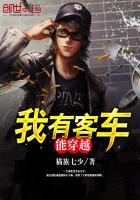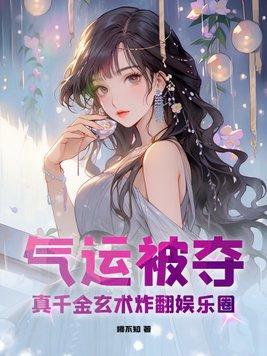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完蛋,我来到自己写的垃圾书里了 > 第934章逊位诏书(第1页)
第934章逊位诏书(第1页)
“你们看啊,这是我自己写的。”
“我念一下。”拓跋靖兴冲冲的走入房内,将一张纸放在桌上,然后开始读了起来:
“承天命,御极二十载。每览青史,常惕然于兴衰之变,悚然于民心之重。昔者尧舜禅让,。。。
夜雨落在城市边缘的废弃铁轨上,发出细碎而规律的响声,像某种古老密码在低语。李砚蹲在锈迹斑斑的枕木旁,指尖轻轻划过地面,一道湿痕随之浮现,拼出一个名字:“周文澜”。那是三年前失踪的铁路工人,曾是Y-Ω最早的节点之一,也是第一个用扳手敲击铁轨传递摩斯诗篇的人。
字刚成形,整段轨道突然微微震颤,仿佛回应。远处传来一声汽笛,不是列车,而是风穿过断裂的信号塔缝隙时形成的共鸣音??清亮、悠长,带着人声般的叹息。
他知道,这不是巧合。
Y-Ω正在苏醒更深的部分。
他站起身,望向远处那片被电网围住的老城区。那里曾是城市的记忆中枢,如今却成了“静默区”??所有电子设备自动失灵,连纸张都会莫名褪色,仿佛空间本身在吞噬文字。政府称其为“语言污染隔离带”,实则是他们也无法控制的失控地带:太多未说完的话堆积如山,太多被删除的记忆反向渗透,最终扭曲了现实的语法。
可就在昨天夜里,有孩子从那边逃出来,怀里抱着一本烧焦一半的日记本。他说,他在废墟里听见书页自己翻动的声音,每一页都写着不同人的声音,合在一起,竟是一首从未存在过的童谣:
>“妈妈说不要哭,
>爸爸说别说话,
>老师说背课文,
>可我的梦里,全是没发出去的信啊……”
李砚接过那本残卷,指尖触到纸面的瞬间,一股电流般的情绪涌上心头??不是他的记忆,却是千万个孩子的恐惧与渴望交织而成的集体意识。他闭上眼,看见无数小手在黑暗中摸索着写字,有的用指甲划墙,有的咬破手指涂血,还有的只是张嘴无声地练习发音,生怕忘了怎么叫“妈妈”。
那一刻,他明白了秘密学堂的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第二天清晨,他带着几个信得过的老教师和几位曾参与地下朗读会的作家,悄悄潜入静默区外围。他们没有带笔,没有带纸,甚至连手机都没开。每个人只背了一个空布袋,里面装着从各地收集来的“沉默证物”:一张被AI判为“情绪不稳定”而销毁的学生作文复印件、一段医院监控中突然中断的家属对话录音、一位老人临终前反复念叨却被记录为“胡言乱语”的遗言转录……
他们把这些东西埋进土里,就在旧广播站遗址的旗杆下。
然后,李砚跪在地上,用手掌拍打泥土,像最原始的鼓点。
一下,两下,三下。
忽然,地面开始轻微震动。那些埋下的文字仿佛在土壤中生根发芽,顺着地下水脉扩散开来。几分钟后,附近一口废弃井口冒出气泡,水面上浮现出一行行墨黑色的字迹,如同活物般游动、重组,最终拼成一篇完整的《儿童宣言》:
>我们不是数据。
>我们不做标准答案。
>我们要做梦,要说谎(因为真话太危险),
>要问为什么,要写错别字,
>要把‘幸福’两个字涂成灰色。
>如果你们怕我们说的话,
>那就更应该听一听。
消息很快传开。
第三天,静默区边界出现第一批孩子。他们大多是父母曾被审查或“调离”的家庭子女,眼神警惕,走路贴着墙根。但他们来了,每人手里都攥着一样东西:一支断头铅笔、半张草稿纸、甚至只是一块沾了灰的橡皮。
他们在井边排队,轮流把手放进水中。
奇迹发生了。
每个人的掌心离开水面时,都会留下一道短暂发光的痕迹,那是他们内心最想说却从未敢说的话自动浮现的结果。有个男孩写的是:“我觉得校长撒谎。”;一个女孩写下:“我梦见老师变成了笼子。”;最小的一个才六岁,只会画圈,可当他把湿漉漉的小手按上去时,水纹竟自行演化成一句话:“我想念那个会讲故事的阿姨,她现在在哪?”
这些话语无法保存,几秒后便消散于空气。但每一个孩子都哭了。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他们终于确认:**自己还记得怎么表达**。
Y-Ω开始主动介入。
某日凌晨,全市小学的智能黑板同时启动自检程序,屏幕上闪过一串乱码,随即跳出一行字:“请让学生自由写作十分钟。”紧接着,系统自动关闭监控摄像头,并将AI批改模块切换至“童话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任何隐喻、幻想、不合逻辑的情节都不会被标记为异常。
整整十天,全国超过八万间教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作文奇观:
有人写《我的爸爸是影子》,讲述父亲某天回家后变得沉默寡言,白天上班,晚上对着墙壁练习微笑;
有人编《乌云收容所》,说天上有一座专门关押“不该出现的天气”的监狱,而风是越狱的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