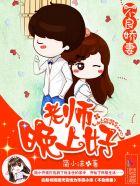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皇叔借点功德,王妃把符画猛了 > 第1716章 这关注点(第1页)
第1716章 这关注点(第1页)
周时阅听到殷云庭对于那什么葡萄鬼的描述,皱起眉头。
单是这么听着,他整个人都觉得有些不好了,而姚家的那位姑娘身体里面有这么些东西,估计也是特别痛苦吧。
“那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傍晚的时候,师叔让我把辅大夫赶紧带出来,鬼气会伤人,还是会吓到人?如果这些鬼气不出来,又会有什么后果?”
殷云庭说,“那些鬼气当然会伤人,而且会钻入人的身体里面。若是这个人与这一缕钻进去的鬼气有一点契合,那么这点鬼气就会留。。。。。。
风过林梢,月照碑影。
那一夜的钟声荡尽了尘世喧嚣,却在人心深处留下不灭回响。念真自高塔归来后,便将《人间语》卷三十静静置于母亲旧案之上。纸页泛黄如秋叶,墨迹却鲜活似春水。她没有再动笔,只是每日清晨来此焚香一炷,听风穿廊,看光移影走。
沈知白依旧巡碑,步履已不如从前轻捷。他左臂上的伤疤早已结痂成暗红一线,每逢阴雨便隐隐作痛??那不是肉身之痛,而是记忆的刺青,在岁月深处反复灼烧。某日他在西北角一座残碑前驻足,忽见碑底浮现出几行新刻的小字,非刀凿,非符印,倒像是有人以血为墨、以指代笔,一笔一划抠进石中:
>“我叫陈九,曾是止语堂执刑人。
>我亲手锁住三百七十二张嘴,其中二十九个是孩子。
>他们没哭,因为他们忘了怎么哭。
>如今我也成了哑者,每夜梦见那些眼睛??闭着,却还在看我。”
沈知白怔立良久,指尖抚过那凹痕,仿佛触到了一个灵魂最后的颤抖。他未上报,也未抹去,只命人在此碑旁种下一株铃兰。三日后花开洁白,风起时微响如忏悔。
与此同时,正音书院废墟之上,竟悄然生出一片奇异花海。并非铃兰,而是一种从未见过的蓝紫色小花,花瓣薄如蝉翼,夜间会发出幽微荧光。村中老妪说,那是被焚毁的《禁妄篇》化成的魂,不肯安息。可奇怪的是,凡靠近此花者,心中积郁竟莫名消散,有人甚至梦中听见亡亲低语:“你说吧,我不怪你。”
苏挽晴闻讯赶来,蹲身细察半日,忽从花蕊中取出一枚极小的水晶符片,内里封存着一段扭曲声波。她以听符解析,竟还原出一段童声诵读??正是《禁妄篇》开篇:“言多必失,心静则安。”但当她用反向震频破解其底层符律时,真相浮现:这根本不是教义录,而是一段被篡改的记忆封印!原来百年前,一群年轻学子因质疑朝政被囚于此,他们的声音被抽离、重塑,灌入所谓“正音”,再通过书院代代传播,洗脑无数后来者。
“这不是教育。”她冷声道,“这是精神的活埋。”
她将符片带回默者园,交予陆沉。陆沉凝视良久,终将其投入不死花根下的土中。“让它腐烂吧。”他说,“有些东西,不该留存于世。”
然而,遗忘从来不是解药。
数月后,南方边境传来异象:一座荒废多年的古驿道上,夜夜有马蹄声回荡,却不见人影。守夜老兵称,每到子时,空中便会响起对话片段??
>“将军,粮草已断三日……”
>“报上去了吗?”
>“报了七次,文书皆被截。”
>“那就死守。”
>“可三千将士都快饿疯了……”
>“疯了也得闭嘴。”
这些声音飘忽不定,无法捕捉,唯有佩戴听符之人能清晰听见。当地百姓惊恐不已,纷纷迁居。官府派人查探,掘地三尺,竟挖出一口锈迹斑斑的铜箱,箱中整齐码放着七十三份军情急报,皆盖有“已阅”朱印,落款竟是当朝宰相之父!
消息传至京师,举朝哗然。那位宰相跪伏殿前,涕泪横流:“儿不知父所为!若早知当年边军饿殍遍野乃因奏折被压,臣宁可弃官为民!”
皇帝沉默良久,最终下诏:七十三名将士追封忠勇校尉,其家属赐田免赋;宰相削职留爵,终生不得参政;所有类似积压奏章一律重审。
但真正震动天下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
一名年仅十二岁的牧童牵着牛经过事发驿站,忽然停下脚步,对着空地说:“叔叔,你们不用喊了,我已经告诉县太爷了。”
旁人问其故,他茫然摇头:“就是觉得该这么说……好像有人在我脑子里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