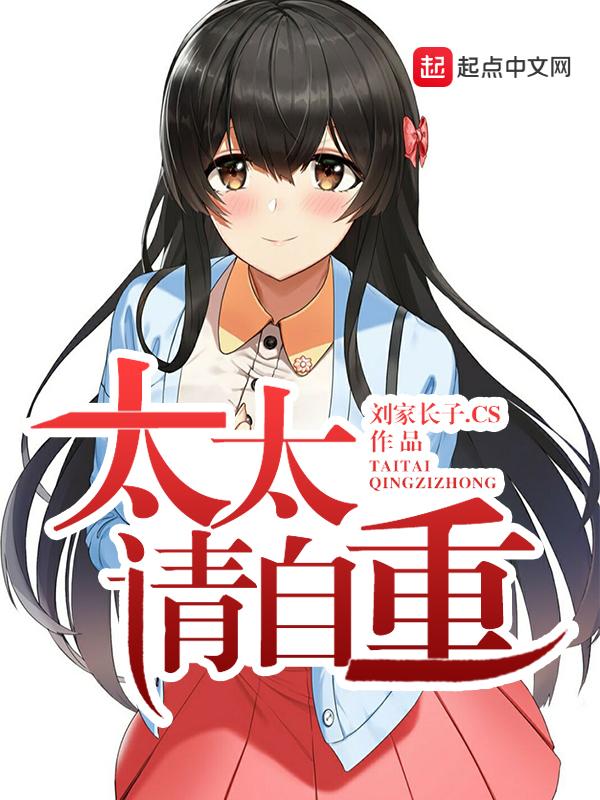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都重生了谁考公务员啊 > 第705章陈委员的过年三件套(第2页)
第705章陈委员的过年三件套(第2页)
AI的第一位真人对话者,是内蒙古阿拉善那位牧民妇女。她对着麦克风磕磕巴巴地说:“我想……我想学……历史。”
AI温柔回应:“我们可以从您小时候的故事开始讲起,每个人的历史,都值得被记住。”
那一刻,技术不再是冰冷的代码,而成了倾听的耳朵。
然而,正当一切看似步入正轨时,一场更大的危机悄然逼近。
六月中旬,某权威媒体刊发评论文章《警惕“民间教育自治”背后的意识形态风险》,文中虽未点名,但多处影射“某些平台以普惠之名行松散管理之实,放任非专业人员传播未经筛选的知识内容,可能造成价值观偏差”。文章引发广泛转载,舆论风向一夜逆转。
有家长投诉平台上有志愿者讲解“女性独立”话题,认为“不适合未成年人”;
有地方教育部门要求学校不得推荐学生使用外部学习资源;
更有一位退休干部在接受采访时直言:“教育怎么能交给老百姓自己搞?那还要国家干什么?”
压力如山压来。数家合作企业暂缓投放广告,两位核心讲师因“家庭原因”退出,甚至连办公室所在的园区物业也开始询问:“你们是不是涉及敏感业务?”
那晚,陈着独自留在公司,翻阅着平台上百万条学习记录。他看到一个安徽留守儿童连续三年每天打卡朗读课文,只为等外出打工的母亲回家时能听她读一篇作文;看到一个东北下岗工人通过学习电工课程,如今已在小区里义务帮邻居修电器;看到一个新疆小伙用平台上学到的普通话考取导游证,带着外国游客介绍家乡美景……
这些真实的生命轨迹,怎会是“风险”?
他打开直播,没有预告,没有标题,只是静静地坐在镜头前,身后挂着那幅中国地图,星星点点,遍布城乡。
“各位,”他说,“我知道最近很多人在问:我们到底是谁?我们要做什么?”
他停顿片刻,声音轻了下来:“我们不是对抗体制的人,也不是想取代学校的组织。我们只是相信,一个人想读书,不该被拦在门外;一个母亲想认字,不该被丈夫砸掉平板;一个孩子想上学,不该因为住在山里就被放弃。”
“有人说我们制造混乱。可什么是秩序?是所有人都按同一个模子长大吗?还是允许有人慢一点、偏一点、弯一点,但仍能走到光里?”
“如果我们连‘我想学’这句话都要审查,那我们配谈什么现代化?”
直播持续了两个小时,全程无删减上传。第二天,数十所高校师生自发组织线上观影会,将其作为“公民社会与公共教育”课程案例讨论;三位院士联名致信主管部门,呼吁理性看待民间教育创新;更有超过十万用户在同一时间打开平台,集体打卡学习,形成一场无声的声援。
一周后,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在例行发布会上表态:支持社会各界依法依规开展数字化终身学习探索,强调“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身就包含对知识的渴求”,并指出“引导比禁止更重要,服务比管控更有效”。
风暴退去,留下更深的思考。
陈着开始推动一项新计划??“共学入编”。不是让平台被收编,而是主动将成熟课程体系、师资培训标准、技术架构无偿捐赠给各地社区学院、老年大学、职教中心,帮助它们搭建本地化数字学习系统。他称之为:“把火种还给土地。”
湖南浏阳的一位乡镇干部在试点会上感慨:“以前我们总想着怎么管住老百姓,现在才发现,他们早就走在前面了。”
秋天来临时,平台用户突破一千五百万。而在西部多个省份,由村民自主运营的“共学小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有的建在废弃校舍,有的设在村委会活动室,甚至还有建在流动图书车上的。每个小屋都配有太阳能电源、卫星网络接收器和一批预装课程的平板电脑,完全由当地人轮流管理。
四川大凉山的一个彝族少年成了当地最年轻的“共学管理员”。他在日记里写道:“以前我觉得山外的世界和我没关系。现在我知道,只要我能连上网,我就和整个中国在一起。”
年终总结会上,团队播放了一段内部短片。镜头扫过全国各地的共学现场:东北雪原上,一群老人围着火炉学用微信视频拜年;海南渔港边,渔民们在归航后聚在一起听海洋法规课;深圳城中村的出租屋里,外来工夫妻一边哄孩子睡觉,一边低声背诵积分落户政策条款……
片尾,是热依汗老太太又一次来到村口卫生院。这次,她不仅自己填好了表格,还主动帮另一位维吾尔族大妈翻译医嘱。医生笑着说:“您现在是我们这儿的‘编外导诊员’了。”
她咧嘴一笑,皱纹里盛满阳光:“我不是编外,我是正式学员。”
会议室里响起掌声,有人悄悄抹泪。
陈着站起身,只说了一句话:“明年,我们要让每一个想学的人都能找到入口,不管他住在哪儿,多大年纪,有没有文化,有没有人支持。”
散会后,他独自走上天台。夜空清澈,星河浩瀚。他掏出手机,打开平台首页,看着那句始终未变的标语:
**“你想学会的,从来都不是知识本身。”**
风吹过耳畔,仿佛千万人的低语汇成一句话:
“我还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