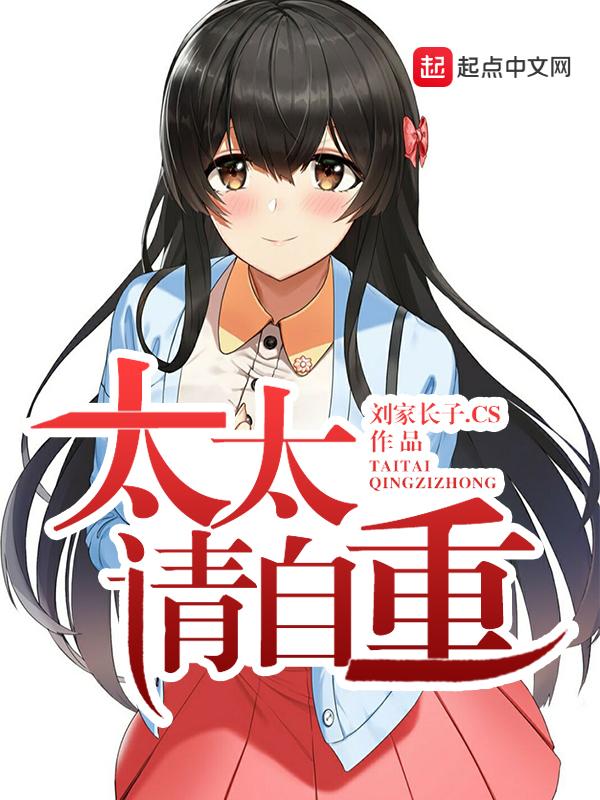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都重生了谁考公务员啊 > 第705章陈委员的过年三件套(第1页)
第705章陈委员的过年三件套(第1页)
以陈培松宦海浮沉的阅历,他都花了好长的时间,才能接受这个事实:
不是易家和溯回关系不一般。
而是易家公主和自家儿子,似乎有一点不同寻常的关系。
儿啊,你疯了吗?
想让你爹进去就。。。
陈着把那本手工册子轻轻放在办公桌上,窗外的雪还在下,细密而安静,像是无数未被说出的话,缓缓落在人间。他起身泡了杯茶,茶叶在热水中舒展,如同那些在屏幕前一点点打开世界的身影。茶香氤氲,他忽然想起热依汗老太太信里那句“让我活得像个人”,心头一震,仿佛又被什么击中了一次。
他打开电脑,调出平台最新数据看板。用户总数已突破一千二百万,日均活跃学习时长达到四十七分钟,最活跃的时段不再是清晨或深夜,而是午休、通勤、工间休息??知识正悄然嵌入生活的缝隙,成为一种日常呼吸般的存在。更让他动容的是,“共学引路人”的数量突破了八万,他们中有退休教师、残疾青年、单亲妈妈、返乡农民工,甚至还有几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坚持每周录制一节识字课。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林小雨。
“陈着,你得看看这个。”她的声音有些发抖,“广西那边……出事了。”
他立刻点开她发来的链接。是一段短视频,拍摄于桂西北一个偏远山村的小学教室。画面里,十几个孩子围坐在一台老旧投影仪前,正在观看平台上的一节数学课。老师是个年轻志愿者,正用动画讲解分数的概念。突然,门口传来一阵嘈杂声,几个穿着制服的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人手里拿着文件,说是“接群众举报,该教学点涉嫌非法集会、传播未经审核的教学内容”,要求立即停止使用平台资源,并查封设备。
镜头晃动,孩子们惊恐地缩成一团。有个小女孩抱着平板不肯撒手,哭着说:“这是我的作业!我明天要交的!”老师试图解释,却被粗暴打断。视频最后定格在一块黑板上,上面还写着刚讲到的一道题:12+14=?
陈着盯着屏幕,久久没有说话。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当光亮照进黑暗,总会有人觉得刺眼。
但他没想到,第一记重拳竟打向孩子。
他拨通王磊电话:“马上启动‘护苗计划’应急响应,我要所有技术日志、课程备案记录、合作机构资质,在两小时内整理成公开报告。另外,联系法务团队,准备发起公益诉讼。”
“我们真要告政府?”王磊语气迟疑。
“不是告政府,”陈着声音低沉却坚定,“是请他们回到规则里来。我们每一步都合规备案,课程全部开放审查,连广告都没有打过一句。如果这都叫‘非法’,那什么叫合法?”
挂掉电话后,他没有发微博,没有写长文控诉,而是登录平台后台,悄悄将那个被查封教室的IP地址设为“特别关注用户”。系统自动推送了本地化课程包,并开启一对一在线辅导通道。他还给那位抱着平板哭泣的小女孩留言:“你的作业我看到了,答案是34。你做得很好,别怕。”
然后,他在直播平台发起一场名为《谁在阻止孩子上学》的特别对话,邀请了教育学者、基层教师、法律专家和那位被驱赶的志愿者老师连线。直播间没有煽情音乐,没有悲情叙事,只有事实陈述与条文对照。当学者逐条指出所谓“非法集会”根本不适用于正常教学活动时,当律师展示全国已有三百多个类似共学点获得地方教育局默许支持时,评论区开始沸腾。
“我在贵州支教三年,没见过哪个孩子是因为学知识被赶出门的。”
“我女儿在县城小学,教材之外的东西一律不许看,可她才八岁啊!”
“你们查封的不是设备,是希望。”
更有数百名用户自发转发自己当年失学的照片,配上一句话:“如果那时候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会不会不一样?”
直播进行到第三小时,广西当地教育局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经查,涉事教学点属村民自发组织的假期补习班,未在主管部门备案,工作人员执法过程中存在方式不当问题,已责令整改并道歉。同时表示,将尽快出台民间助学行为的规范指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补位。
风波平息得比预想快,但陈着心里清楚,这只是表层涟漪。真正的暗流,藏在那些尚未被照亮的地方。
几天后,他收到一封来自甘肃临夏的邮件。寄信人是一位回族妇女,名叫马秀兰。她说自己四十岁才开始识字,靠每天凌晨五点起床听平台上的拼音课,半年后终于能读简单的新闻。后来她发现村里很多妇女和她一样不识字,便自费买了几台二手平板,组织大家晚上一起学。
“我们不敢挂牌,也不敢宣传,就在院子里点盏灯,围一圈人。有人笑我们老了还折腾,可我觉得,只要还能学会一个字,就不算晚。”她在信中写道,“但上个月,丈夫说我‘不安分’,砸了平板,还说再学就离婚。”
邮件末尾附着一张照片:夜里,几个女人蹲在院墙角落,借着手机微弱的光,低头抄写生词表。她们的脸模糊不清,唯有手中的笔,在纸上划出清晰的痕迹。
陈着把这封邮件打印出来,贴在公司会议室的墙上。旁边是他写的一句话:“教育的权利,不该由婚姻决定。”
第二天,平台上线“隐秘学习者”保护机制:用户可选择匿名模式,隐藏身份信息、学习轨迹与社交互动;所有课程支持离线缓存,即使断网也能继续学习;新增“紧急备份”功能,一旦检测到设备异常关机或强制删除,系统将自动上传最新学习进度至云端加密空间。
与此同时,“共学伙伴”联合妇联、公益组织发起“暗夜灯火”行动,为身处困境的成年学习者提供心理支持、法律援助与替代学习工具。首批发放的一千套“静音学习包”包含降噪耳机、太阳能充电灯、防水笔记本和平板支架,专为夜间偷学、避人耳目者设计。
一位云南怒江的傈僳族妇女收到包裹后录了一段语音:“我现在每天等娃睡了才敢学,戴上耳机,声音调到最小,就像在做梦。可我知道我不是梦,因为我昨天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
陈着听着这段录音,眼眶发热。他忽然意识到,他们做的早已不只是教育平台,而是一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的避难所。
春天再次来临的时候,平台迎来一次重大升级。基于百万用户的学习数据,“共学AI导师”正式上线。它不像商业化的智能助手那样追求效率最大化,而是专注于“理解落后”。它知道一个五十岁农民学乘法口诀需要多久,明白一个听力障碍者分辨“z”和“zh”的困难,更能识别出那些反复退出又登录的账号背后,是一个人在羞耻与渴望之间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