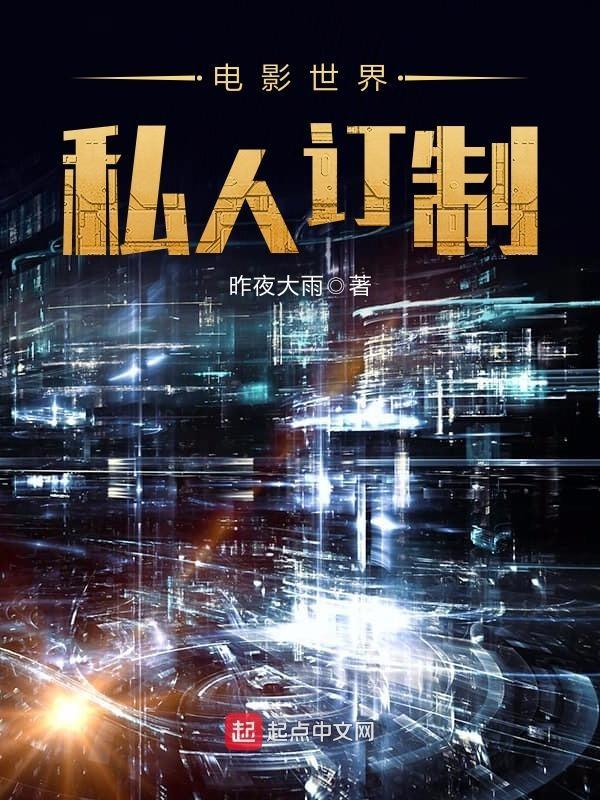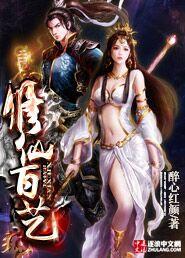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在现代留过学 > 第一千零八十章 京观(第3页)
第一千零八十章 京观(第3页)
一个孩童率先开口:“民之痛楚,非政之装饰。”
接着是妇人:“不是天灾害人,是人害人。”
然后是老者:“彼以遗忘治天下,吾以记忆抗暴政。”
越来越多声音加入,汇成洪流??正是《十罪书》全文,一字不差,一句不断。
人群自动分开,数十名身穿粗布的男女捧着竹简、纸卷、木牌走出,齐声朗读。有人手持铜铃,摇动不止;有人肩扛陶罐,罐上刻“井”;更有七名少年抬着一口仿制的“直言钟”,虽无声响,却昭示信念。
禁军欲上前镇压,却被围观百姓层层挡住。老人挡在孩子身前,农夫挽起袖子,连平日唯唯诺诺的小贩也站了出来,齐喊:“我们要听真话!”
甘兰进闻讯震怒,下令格杀勿论。箭雨即将射出之时,忽见皇宫方向飞驰而来一骑快马,使者高呼:“圣上有旨??暂缓行刑,押回再审!”
全场哗然。
原来,就在昨日夜间,紫衣宦官张念祖将《烬语》残稿与李承恩提供的密信副本,悄然投入皇帝寝宫外的奏匣,并附短笺:“陛下若不信,请召见东厂暗探首领,问他近年截获多少忆堂文书;请查阅户部账册,看是否有‘删案银’进出;请派人查验泉州废墟,是否真无尸骨残留。”
皇帝年迈多疑,却尚未完全昏聩。他连夜召见心腹查验,果然发现诸多异常:东厂档案库中有大量未上报的民间控诉,户部一笔笔“修缮费”实为贿赂转账,甚至有地方官定期进贡“太平祥瑞图”,竟是伪造百姓感恩画像……
铁证如山。
圣旨收回,阿禾暂免死刑,转入天牢软禁。甘兰进虽未立即倒台,但权势动摇,党羽纷纷自保。朝廷下令彻查忆堂冤案,开放部分档案供学者参阅。民间自发组织“述史会”,鼓励长者口述往事,孩童记录家史。
三个月后,春雨绵绵。
阿禾被秘密释放,名义上“病逝狱中”,实则由“十四井盟”接应,藏身于江南一处书院。他化名“沈默之”,教授蒙童识字作文。课堂上,他不再讲经义策论,而是带着孩子们走进田间,采访老农,记录旱涝年景、赋税变化、官吏作风。
他在院中挖了一口井,命名为“言泉”。井边立碑,刻八个大字:“声出于渊,道生于民。”
每逢月圆之夜,他会取出铜铃,轻轻一摇。有时风静无声,有时铃音激荡,仿佛回应来自四方的呼唤。
一年后的清明,他重返泉州。
贡院遗址已建起一座小型纪念馆,由幸存家属与民间捐资兴建。馆内陈列《烬语》抄本、遇难者遗物、匿名寄来的供词与账册。最中央,是一座由三百七十块碎瓷拼成的壁画??每一块瓷片都来自当年火场残瓦,拼出的是陈文昭临终前写下的最后一句诗:
>“纵使灰飞烟灭,吾志不堕尘泥。”
阿禾站在画前,久久不语。身后传来脚步声,一位白发老太太走近,递给他一本手抄册子:“这是我孙女写的,《我家的故事》。她说,以后每年清明,都要来这里读一遍。”
册子翻开,第一页写着:“我太爷爷叫陈文昭,他是解元,他说天下该有公道。我没见过他,但我替他活着,替他说下去。”
阿禾合上册子,仰望天空。
云层裂开一道缝隙,阳光倾泻而下,照在纪念馆屋檐的铜铃上。铃随风动,清音袅袅,传向远方。
他知道,这场战争远未结束。甘兰进仍在朝堂挣扎,野忆坛仍有成员被捕,许多井铃再度沉寂。但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倾听,只要还有一个孩子肯写下真实,记忆就不会死去。
他抚摸胸前的铜铃,低声说:
“我会继续走。
走到山穷水尽处,
走到史官不敢写的地方,
走到人们终于敢大声说出‘我记得’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