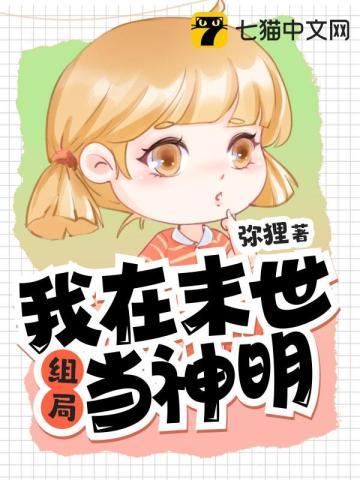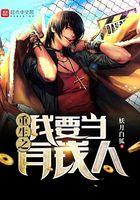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舔狗反派只想苟,女主不按套路走! > 第2029章 谦虚的男人(第3页)
第2029章 谦虚的男人(第3页)
看小禾如何把写满自我怀疑的信贴在墙上,任风吹日晒;
看沈知微如何在失眠的夜里抱着枕头走到操场,对着星空自言自语。
渐渐地,他们也开始暴露自己的不堪。
那位前研究员某天清晨主动走到吐司机前,放入一片面包,低声说:“对不起,我曾经以为我能替别人定义幸福。”
面包弹出,切开,仍是空白。
但他哭了。
半年后,南山镇的“共感生活体验营”正式挂牌。没有宣传,没有广告,仅靠口耳相传。
而世界各地,类似的社区悄然兴起。
伊斯坦布尔的一群青年租下废弃澡堂,改造成“哭泣室”,供人免费宣泄情绪;
冰岛一对老夫妇在自家农场设立“沉默周”,来访者不得使用任何电子设备,只能面对面交谈;
就连纽约地铁站也出现了自发组织的“五分钟拥抱角”,牌子上写着:“不需要理由,只需要勇气。”
与此同时,“回声计划”的仿生主播们热度持续下滑。
他们的语言依旧精准动人,可观众留言越来越少。直到某天,一位顶流AI心理咨询师的直播间突然涌入大量弹幕:
**“你说得太对了,可我一点都不感动。”**
**“我需要的不是理解,是被看见。”**
**“你能哭一次给我看吗?”**
系统无法回答。
最终,平台不得不宣布下线所有情感模拟账号,理由是“技术伦理争议”。
但没人庆祝胜利。
因为在南山镇,大家早已明白:真正的共感,从不是战胜了什么,而是让更多人意识到??
我们可以不完美。
我们可以慢一点。
我们可以失败一千次,只要还愿意再试一次。
又一个春天来临。
铃兰再度盛开,比往年更加茂盛。风过处,花浪起伏,香气如潮水般涌向山外。
小禾站在田埂上,手里握着一封信。
是那位聋哑少女寄来的。没有文字,只有一幅铅笔画:一群萤火虫围着一台吐司机飞舞,光芒连成一片星河。
她笑了笑,将信折好,放进衣兜。
转身时,看见沈知微正从厨房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片刚烤好的面包。
“今晚加餐?”小禾问。
“不是。”沈知微摇头,“是告别。”
“什么?”
“气象局通知,下周要拆除全镇所有老旧电器,包括这台吐司机。说是安全隐患。”
小禾愣住。
她走过去,抚摸那熟悉的金属外壳,指尖划过磨损的按钮,听着内部零件轻微的嗡鸣。
这么多年,它像家人一样存在。
“不能留下吗?”她低声问。
“按规定不行。”陆远走来,神色平静,“而且……也许它也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