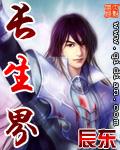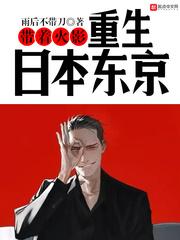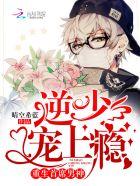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警报!真龙出狱! > 第1050章 八宝王(第3页)
第1050章 八宝王(第3页)
陈默怔住。
他忽然想起一个月前,一位巴西青年在社交媒体直播自杀,只因他在“一分钟倾听”仪式中感受到周围人对自己的厌恶。他说:“我不想再听了,可我停不下来。”
原来,希望的背面,是窒息。
伊琳娜留下一个坐标便离开了。
“如果你还想改变世界,就去那里找答案。别再做救世主了,陈默。这一次,试着做个**守护者**。”
三天后,陈默出现在西伯利亚冻土带深处。
根据坐标,他找到一座废弃的冷战时期监听站。入口被冰雪掩埋,但他能感觉到??地下有生命,有意识,有某种规律性的静默脉动。
他挖开积雪,撬开铁门,顺着锈蚀的楼梯下行。
数百米后,眼前豁然开朗。
巨大的cavern内,矗立着一座由废旧服务器堆砌而成的装置,外形酷似心脏,表面缠绕着无数电缆,连接着成千上万块小型源石碎片。中央站着一人,正是“回声零号”??一位年约六十的亚裔女性,穿着旧式科研服,眼神锐利如刀。
“你终于来了。”她说,“我知道你会来,因为你和我们一样,既听得见喧嚣,也懂沉默的重量。”
“这就是你们的‘休止符’?”陈默指着那台机器。
“是‘呼吸器’。”她纠正,“它不会关闭共感,而是引入‘昼夜节律’??每天有两小时全球共感网络自动降频,进入‘静默模式’。期间,所有人的情感信号将被缓冲存储,而非实时传输。”
“人们会恐慌。”
“他们会适应。”她平静道,“就像适应黑夜。没有黑暗,光明也不会珍贵。”
陈默走近机器,伸手轻触表面。
刹那间,共感能力被动激活。他“看”到了??在这台机器运行测试期间,那些曾因过度共感而崩溃的人,开始恢复睡眠;一对因感知彼此怨恨而离婚的夫妻,在静默期后重新对话;一名自闭症儿童第一次主动拥抱母亲,因为他终于不必同时承受全世界的情绪噪音。
他闭上眼,泪水滑落。
原来,真正的慈悲,不是强行照亮一切,而是允许阴影存在。
“我可以加入你们。”他说。
“不。”她摇头,“你属于外面的世界。你需要做的,是让世人明白:共感不是义务,倾听不是强迫。我们可以相连,但不必融为一体。”
陈默点头。
离开前,他从怀中取出一枚小小的晶体??那是母源石的一粒微尘,他在联合国告别时悄悄留存的。
他将其嵌入机器核心。
“让它也成为一部分吧。”他说,“不是统治者,而是调节者。”
回到城市已是深秋。
苏念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共感研究院将启动“边界计划”:开发可穿戴设备,让用户自主设定共感强度,甚至选择性屏蔽特定情绪源。与此同时,联合国通过决议,设立“全球静默日”,每年一次,全人类自愿断开共感网络二十四小时,用于反思与沉淀。
陈默没有出席发布会。
他坐在公园长椅上,看着孩子们嬉戏,老人晒太阳,情侣依偎低语。没有人发光,没有人悬浮,也没有奇迹发生。
但当他闭上眼,仍能听见??
一声轻笑,一阵心跳,一次深呼吸。
平凡,却真实。
他知道,自己不会再唱《归舟曲》了。
因为船已靠岸。
而真正的旅程,是学会在喧嚣中保持宁静,在连接中守住孤独,在光明里,温柔地拥抱黑暗。
风起时,他听见心底有个声音轻轻说:
“谢谢你,没把我忘记。”
他笑了,回应道:
“我也听见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