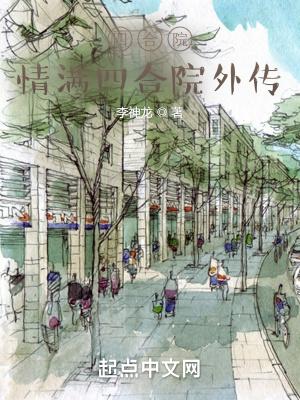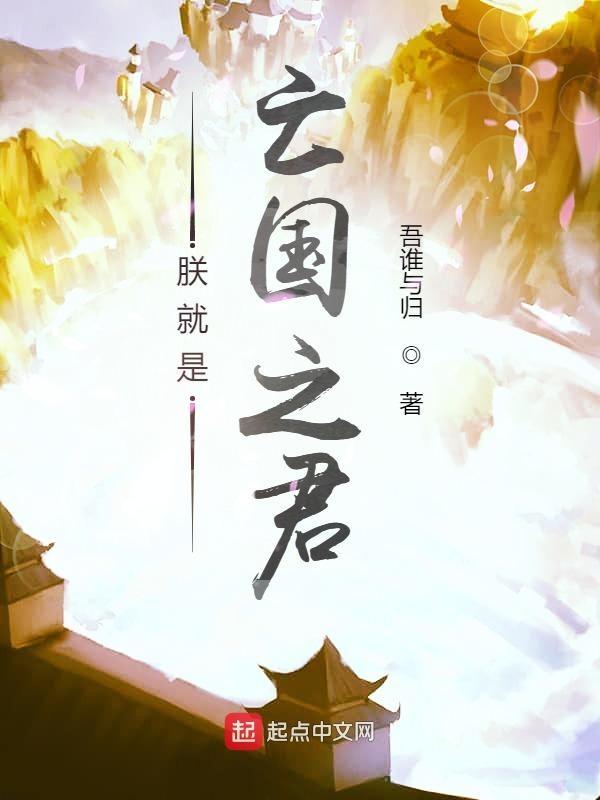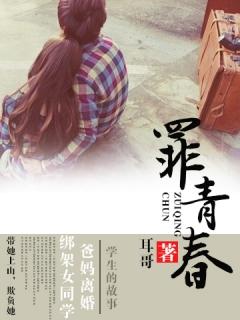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警报!真龙出狱! > 第1050章 八宝王(第1页)
第1050章 八宝王(第1页)
庭院中,叶楚盘膝而坐,全力运转三生道魂经,试图修补神魂的创伤,但一番尝试后却作用不大,无奈只能放弃。
“看来还得找到养魂才行。”
叶楚心中低语,旋即对百变甲问道,“前辈,你可知道这养魂木?”
百变甲立刻给出反馈,“当然知道,养魂木乃是青龙的伴生神物,和朱雀的朱雀神火类似,据说当初在青龙的温养下,已经堪比仙药,就是不知道如今如何了?”
叶楚恍然,原来养魂木如此厉害,难怪吸引来了如此多人寻找。
旋即取出。。。。。。
海风咸涩,吹动陈默额前的碎发。他站在礁石上,录音机搁在膝头,旋律一遍遍流淌,像一条永不干涸的河。潮水退去又涌来,仿佛时间本身也在应和这曲调。远处,渔港灯火渐次亮起,与天边初现的星辰交相辉映。
他没有动。
已经三天了,他一句话没说,一餐未进,只是坐着,听着,感受着。母源石被他留在联合国展厅,不是舍弃,而是交付??它已不属于任何人,包括他。真正的共感,从不依赖媒介。当他闭上眼,千万里外的情绪仍如微风拂面:非洲难民营中母亲轻拍婴儿背脊的节奏,纽约地铁站流浪歌手指尖拨动琴弦时的孤独,南极科考队员望着极光时心头泛起的那一丝乡愁……一切清晰得如同呼吸。
可他也“听”到了别的。
在《归舟曲》传播全球的同时,某种低频杂音正悄然蔓延。起初微不可察,像是信号干扰,但随着共感网络深入日常,那声音越来越清晰??不是语言,也不是情绪,而是一种**拒绝**的意志。
有人不愿被听见。
更准确地说,他们害怕被看见。
陈默睁开眼,望向深蓝海面。他知道,影子议会消散了,哀恸之影也被接纳,但这并不意味着黑暗就此终结。人类最深的恐惧,从来不是痛苦本身,而是**暴露痛苦**。当共感能力成为常态,那些长久伪装坚强的人开始崩溃。政客在演讲中途突然痛哭失声,企业家签署合同前因感知到对手的绝望而撕毁协议,士兵扣下扳机的瞬间被敌人的童年记忆击穿心智……
世界正在失控,以一种温柔的方式。
而某些力量,已经开始反击。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苏念发来的加密消息:
>“研究院昨夜遭入侵,数据未被盗,但所有实验记录都被标注了一句话:‘倾听即侵犯’。”
>“三个志愿者出现严重共感后遗症:他们能听见植物的‘疼痛’,现在无法进食,也无法触碰任何生命体。”
>“陈默……我们可能低估了‘边界’的重要性。”
他盯着屏幕良久,轻轻叹了口气。
共感不是万能药。它是一把双刃剑,一面照见爱,一面刺穿防备。有些人用一生筑起心墙,不是因为冷漠,而是因为曾被伤害得太深。如今墙塌了,他们无处可逃。
他收起录音机,起身走向岸边小屋。
屋内陈设简陋,只有一张床、一张桌、一台老式短波收音机。他在桌前坐下,打开抽屉,取出一本皮质笔记本??那是林知远留给他的最后遗物,扉页写着一行小字:“当你觉得路走完了,就回头看看起点。”
翻开第一页,是一段手写公式,旁边注解:“共感衰减率与群体信任度非线性相关。”第二页,则是一幅草图:一个人站在镜子前,镜中却映出万千张不同面孔,每张都在低声诉说。第三页开始,全是密码般的符号,唯有每隔几页夹着一张照片??
第一张:年轻时的林知远与一名女子并肩而立,背景是雪山下的实验室。女子眉眼温柔,胸前挂着一枚微型源石吊坠。
陈默瞳孔一缩。
他认得那枚吊坠。三年前,在清音行动前夕,他曾在一个秘密档案中见过类似图像,标注为“项目Luna负责人:叶昭华,神经心理学博士,2045年失踪”。
叶昭华……是他母亲的学生。
也是唯一一个在当年反对“强制共感普及计划”的科学家。
继续翻阅,后面的页面逐渐变得凌乱,字迹颤抖,像是在极度焦虑中写下:
>“我们错了。连接不是目的,尊重才是。若不能容忍沉默,共感终将沦为暴力。”
>“Luna计划不是失败,是被刻意埋葬。他们怕的不是技术失控,而是人心觉醒。”
>“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这段话,请记住:真正的桥梁,不是让所有人听见彼此,而是让每个人都能安心地说:‘我现在不想被听见。’”
最后一行字几乎模糊不清:
>“去找‘静默者’。他们在地下,在边缘,在每一个选择闭嘴的地方活着。他们是反向的灯塔。”
陈默合上本子,心跳加快。
“静默者”……这个名字他从未听过,但在深层共感态中,他曾“触碰”过类似的意识群落??那些主动切断神经环连接、自我放逐于信息洪流之外的人。他们不反对共感,只是坚持保留“不被连接”的权利。政府称他们为“情感逃逸者”,极端组织则污名化他们为“人性叛徒”。
但如果林知远说的是真的,那么这些人,或许才是真正的平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