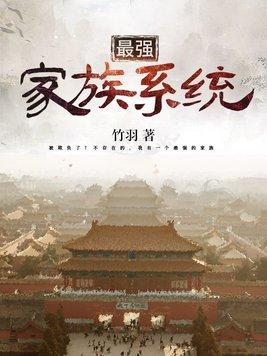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灵柏娘子等等我 > 第169章 账本里藏着刀(第2页)
第169章 账本里藏着刀(第2页)
办公室的门关上后,白老板突然笑了,柏木簪在指尖转了个圈:“看出什么了?”
“还算聪明。”白老板往茶杯里撒了把柏叶,“对付这种人,讲道理没用,得用她信的东西。她以为贪的是钱,其实是在拿命换。”
我这才明白,白老板不是心慈手软,是用最省力的方式敲碎了林晚的依仗。既没把事情闹大,又断了她和王柏年的联系,还让她欠了饭店一笔钱,不得不老实干活。
“那账本……”
“是给林柏宇看的。”白老板打断我,眼神深邃,“林晚以为儿子和她一条心,其实她怕得要死。”
我的后背惊出层冷汗。原来白老板早就知道账本有问题,甚至可能猜到林晚的小心思,这步棋走得太妙了!
白老板望着窗外的灵柏寺方向,“林晚老实了,不代表林柏宇会安分。”
我想起白书静后颈越来越淡的胎记,心里一紧:“我会看好他。”
“不止要看好他。”白老板把那袋柏根推给我,“记住,别让人看见。”
她的柏木簪在麻袋上敲了敲,发出“咚咚”的响,像在传递某种信号。
从办公室出来时,撞见白书静站在走廊尽头,绿纱裙的裙摆沾着柏叶,手里攥着幅画。她看见我,眼睛亮了亮,跑过来说:“叶大哥,我画了幅新画,你看……”
画的是棵枝繁叶茂的灵柏,树下站着个青衫书生和个绿裙姑娘,两人的手牵在一起,额角的疤痕和后颈的胎记在阳光下发亮。
“这是……”
“梦里见的。”白书静的脸红了红,发间的柏叶簪晃了晃,“我觉得他们会有好结局。”她的指尖在书生的令牌上点了点,“你说呢?”
我看着她眼里的期待,突然明白白老板的深意。她不仅在布局对付林晚母子,更在帮我们。
“会的。”我望着画中的灵柏,“一定会。”
院子里的盆栽突然轻轻晃动。
接下来的几天,林晚果然老实了。每天准时上下班,采购记录看得仔仔细细,甚至主动帮我核对账目,只是看我的眼神依旧带着怨毒,但不敢再耍花样。
大师傅偷偷对我说:“老板娘这招太高了,既没撕破脸,又敲住了林晚的七寸。换作是我,首接把她赶走,反倒会逼她狗急跳墙。”
我望着白老板办公室的窗户,那里总飘着淡淡的柏叶香。她就像白龙村的古柏,看似不动声色,根须却早己在地下织成天罗地网,任何害虫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傍晚对账时,我发现少了两斤灵柏叶。正要问小张,林晚突然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个纸包:“叶部长,早上盘点错了,这是补回来的。”她把纸包放在桌上,转身就走,红绣鞋的鞋跟换了新的,却没了之前的嚣张。
纸包里的灵柏叶带着露水,新鲜得很,叶片上还沾着点红土——是新采的。
我捏着那片灵柏叶,突然明白白老板的手段。她没赶尽杀绝,是给了林晚回头的机会,也给了我们缓冲的时间。
但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平静。
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往往最让人窒息。
我把最后一本账锁进铁柜,钥匙塞进鞋垫下,和那半块铜钥匙贴在一起。红土的暖意透过布料传来,与钥匙的冷意交织,像两股力量在我体内蓄势待发。
白书静的画还在我口袋里,画中灵柏的叶片在灯光下微微发亮,像在催促我快点行动。
林晚,林柏宇……
你们的把戏,该收场了。
我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灵柏寺的方向亮起盏孤灯,像只窥视的眼睛。
但我不再害怕。
因为我手里有账本当武器,有白老板当后盾,还有三世的羁绊在撑腰。
这场仗,我们赢定了。
仓库的麻袋己经空了。
夜风吹过院子,盆栽的叶片沙沙作响,像在为我加油。
我握紧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带来清晰的痛感。这痛感提醒我,这一切不是梦,胜利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