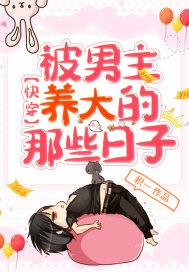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流量下水道,怎么越摆越火了 > 第201章 流量下水道T0屠热度榜不是很正常的吗(第2页)
第201章 流量下水道T0屠热度榜不是很正常的吗(第2页)
昆仑山脚下的临时营地里,《黎明之前》最后一场戏开拍。场景是一座坍塌的边防哨塔,主角在爆炸后爬行数百米,只为把一份边境异常报告送出信号区。剧本原定他在成功发送信息后微笑闭眼,象征任务完成、灵魂安息。
但方盛提出修改:“他不该笑。他应该哭。因为他知道,这份报告也许能救别人,却再也救不回自己死去的兄弟。”
导演沉默良久,点头同意。
拍摄开始。方盛全身涂满泥浆与假血,在零下二十度的地面上一次次匍匐前进。摄像机跟拍,镜头晃动得厉害,如同战地纪实。当他终于将卫星电话塞进雪堆中的信号增幅器时,双手已经冻僵,指甲裂开渗血。他按下发送键,然后缓缓转头望向远方雪山,泪水瞬间结冰。
“卡!”副导演喊停。
没人起身。整个剧组静默伫立,仿佛仍置身于那个不存在却又无比真实的战场。
三天后,粗剪版送审。国家电影局组织专家评审会,现场气氛紧张。有人指出影片结尾过于悲情,建议增加一段“上级嘉奖通报”作为收尾,以体现“正向激励”。
小陆拒绝了。
“这不是需要被奖励的故事,”他在答辩会上说,“这是需要被记住的故事。我们不需要用表彰来证明牺牲的价值,就像不需要用掌声来证明母亲爱孩子一样。”
评审团陷入长时间讨论。最终,影片以“个别镜头需适度弱化视觉冲击”为由通过审查,其余内容全部保留。
消息传来当晚,小陆独自回到办公室,打开了那个铁盒。他取出《春苗计划实录》的硬盘,插入读取器。画面亮起:上世纪七十年代,一群赤脚医生背着药箱翻山越岭,为偏远村庄接种疫苗。其中一个女医生意外滑倒,摔断了腿,仍坚持让同伴抬着她走完最后十里路。村民围着她哭,她说:“别怕,针我都带来了。”
他看得入神,直到手机响起。
来电显示:陈志明。
老人声音沙哑却清晰:“我听说你们要把那卷1976年的片子放出去了?”
“是的,下周‘真实之舟’首映,它会作为开场片。”
电话那头长久沉默,接着是一声轻叹:“也好。当年我们藏它,是为了不让真相死;现在你们放它,是为了让真相活。时代变了啊。”
“您要来看吗?我们可以派车接您。”
“不了。”老人笑了笑,“但我会让孙子去。他对我说,爷爷,你们那一代人做的事,不该只活在黑夜里。”
挂断电话,小陆望着窗外的城市灯火,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所谓传承,并非把火炬交给下一代,而是让每一颗心都成为新的火种。
春节前夕,“回家之路”全国巡映正式启动。首站设在云南怒江傈僳族村落,放映场地是当地小学的篮球场。由于电力不稳定,放映队使用柴油发电机供电,银幕则是用防水帆布手工缝制的。
当晚,上千名村民冒雨前来。当屏幕上出现一位藏族母亲徒步三十公里为孩子背课本的画面时,台下许多妇女低头抹泪。影片结束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颤巍巍走上前,抱住一名志愿者:“谢谢你们,让我们知道自己也是故事。”
类似的情景在全国各地上演。内蒙古草原上,牧民们骑马几十里赶来观看;浙江渔港,凌晨归航的渔船集体调转方向,只为让船员登上岸看一场放映;新疆喀什,维吾尔族孩子们用汉语和维语交替朗诵片尾字幕:“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值得被铭记。”
网络上,#原来我也在电影里#成为热搜话题。数百万用户上传自己生活的短视频:早餐摊主清晨五点生火熬粥、快递员暴雨中护住包裹、护士蹲在医院走廊吃冷饭……这些片段被“真实之舟”团队精选剪辑,制成新春特辑《人间烟火》,在除夕夜全网同步播出。
央视新闻频道罕见地插播了五分钟预告片,并配文:“这不是虚构剧情,这是我们的2023。”
大年初一,《黎明之前》正式上映。
影院内外人山人海。不同于以往大片首映的喧嚣热闹,这一天的观众格外安静。许多人走进影厅前先敬了个礼;退伍军人组团观影,座位号特意选成“1949”“1976”“2020”;一位烈士家属在社交媒体写道:“我爸爸没看过这部电影,但他活成了电影里的人。”
票房一路飙升,单日突破四亿。更令人震撼的是口碑:豆瓣评分9。3,猫眼满分,知乎热榜连续一周置顶讨论“我们为何需要这样一部电影”。一篇题为《当英雄不再被消费》的文章刷屏:“过去我们崇拜超能力,现在我们终于学会尊重凡人之勇。”
小陆没有参加庆功宴。他去了北京西郊的一座烈士陵园,站在一块无名碑前放下一束白菊。风吹起他的衣角,远处传来孩童背诵碑文的声音:
“他们没有留下名字,
但他们留下了和平。”
手机震动,是方盛发来的照片:片场全体工作人员列队敬礼,背景是夕阳下的昆仑山脉。配文只有一句:“我们完成了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