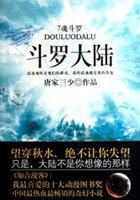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重生:我是县城婆罗门 > 第409章 国内就不可能诞生超过十万亿的公司(第2页)
第409章 国内就不可能诞生超过十万亿的公司(第2页)
“这些纸条……都是你写的?”她指着满屋文字。
少年摇头:“不全是。有些是别人留下的。最近半个月,每天都有人来,写下什么,或者拿走一张带走。有人写了道歉信,给当年批斗过的老师;有人记下父母从未说出口的往事;还有一个老太太,专门来写她丈夫的名字,说‘这辈子没人肯提他,但现在我想让他被人知道’。”
小禾怔然。这间废弃阁楼,竟已悄然成为民间自发的记忆圣殿。
她抽出一支笔,在空白纸条上写下:
>“阿诺说,灯一定要亮着。现在我知道了,灯不在天上,也不在电线里,而在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
将纸条系上绳索,轻轻挂入蛛网中央。
就在此时,楼下骤然响起脚步声,夹杂着对讲机电流音。有人来了。
林晓阳脸色一变:“教育局巡查队,每周四上午例行检查。”
小禾迅速掏出手机,打开whispers离线传输功能,将刚才录下的音频封装成记忆包,设置为“定向扩散模式”??只要附近有开启蓝牙的设备,便会自动接收并继续转发。
“别慌。”她说,“他们可以锁门,但锁不住声音。”
两人从侧窗翻出,沿排水管滑下。落地时,小禾脚下一滑,膝盖磕在石阶上。林晓阳扶她起身,低声问:“你会怕吗?”
她笑了笑:“怕啊。但我更怕闭嘴。”
回到博物馆已是上午九点。老吴正在调试新一批共振腔复制品,准备送往周边乡镇的文化站。见到小禾回来,他抬眼问:“听说教育局报警了?说有人擅闯重点文保单位,破坏展陈。”
“让他们查吧。”小禾坐下揉着膝盖,“真相藏不住了。你看这个。”
她把手机递给老吴,播放那段录音。老人听着听着,手指微微颤抖,最后长长吐出一口气:“知远这家伙……还真把自己活成了电波。”
“不止是他。”小禾说,“还有张桂兰,有杨秀兰,有周维民……有无数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人。他们都在等一句话被听见。”
老吴沉默片刻,忽然转身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尘封已久的木盒。打开后,里面是一卷老式录音带,标签上写着:“1975?清河中学?元旦汇演实录”。
“我一直不敢放。”他低声说,“那天的节目单上有首诗朗诵,叫《春天的声音》,是李老师亲自写的。演出当天她已经……不在了。学生们还是坚持上了台,由班长代替朗读。我偷偷录了下来,藏了快五十年。”
小禾接过磁带,放进修复好的播放机。
咔哒一声,转轴启动。
稚嫩的童声透过扬声器响起,带着时代特有的庄重与天真:
>“风推开了冬天的门,
>雪融化在泥土里,
>我听见种子在地下说话,
>它说:我也想看看太阳。
>老师说,春天不是等到的,
>是用耳朵听出来的。
>所以,请你们都安静一下,
>听??
>春天来了。”
录音结束,满室寂静。
良久,老吴抹了把脸:“该还给他们了。”
当天下午,whispers平台出现一个爆款记忆包,标题只有两个字:【听春】。内容包含林知远遗音、李老师诗稿扫描件、以及那段五十年前的朗诵录音。短短十二小时,转发节点突破十万,甚至有盲童学校将其改编成触摸式音画教材,让孩子们通过振动感知诗句节奏。
与此同时,全国多地涌现“沉默纪念日”活动。人们在公园、校园、广场集体静立一分钟,随后齐声朗读自己心中的“春天之声”。有人读鲁迅的《呐喊》自序,有人背艾青的《光的赞歌》,更多人只是说出一句:“我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