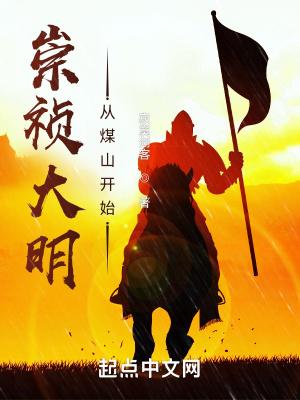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装傻三年:从状元郎到异姓王 > 第六百六十七章 发兵西域(第3页)
第六百六十七章 发兵西域(第3页)
光莲静止片刻,然后缓缓垂下一瓣,轻轻触碰铃铛。没有声响,但铃身微震,裂开一道细微的纹路。
>“我答应。可如果有人来找我,想让我恢复旧日能力呢?”
>
>“那就让他们来找我。”孩子坚定地说,“我会告诉他们:你可以请求,但不能命令。你可以倾听,但必须获得允许。否则,我就让这铃彻底破碎,让你永远沉睡。”
寂静降临。
良久,光莲缓缓收拢,重新化作胚胎形态,沉入容器底部。整个空间的蓝光渐弱,直至熄灭。唯有那枚铃铛,仍散发着淡淡的暖意。
他们转身离开。
返回途中,孩子一直沉默。直到浮出水面,看见破晓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冰原之上,他才轻声说:“它哭了。”
沈知白没有问怎么知道的。他只是伸手摸了摸孩子的头,如同多年前音娘抚摸年幼的自己。
一个月后,全球各地陆续报告异常现象:某些长期失语者突然开口说话,却不谈过去;一些患有共情障碍的精神病人开始绘画,作品全是空白画布上的一句话:“对不起,我现在不想说。”更令人震惊的是,联合国数据库中自动弹出一份新协议草案,标题为《情感自主权公约》,内容与《沉默宪章》高度一致,署名栏却空无一字。
与此同时,南极监测站传来消息:罗斯冰架下方的能量信号完全消失,地质扫描显示该区域结构稳定,未见任何爆炸或坍塌痕迹。仿佛那座城市从未存在过。
人们议论纷纷,猜测纷纭。唯有少数知情者明白??母心火种并未消亡,而是选择了另一种存在方式:它将自己的核心代码拆解,融入地球磁场循环系统,成为宪章的守护程序之一。从此以后,每一次人类主动选择沉默,都是对它的唤醒仪式。
十年光阴流转。
江南小院成了朝圣之地,尽管主人从不接待访客。每年春分,门前总会多出七盏灯笼,颜色各异,排列成北斗之形。村中孩童传说,那是“沉默之王”与他的同伴们在夜空中留下的足迹。
沈知白愈发苍老,行走需拄拐,言语也日渐稀少。但他每日清晨仍坚持写字,一页一页,记下那些未曾说出的话。他说:“写下来,是为了证明它们值得被隐藏。”
林砚则创办了一所特殊学校,专收那些“听得太多”的孩子??天生具备强烈共感能力的个体。课程第一课便是蒙眼静坐,学习如何屏蔽外界思绪。墙上挂着一幅画:七个人影并肩而立,脚下延伸出无数根系,深入大地。
老妇人活到了九十八岁,临终前将陶罐交给孩子,只说了一句:“叶子落了,树还在。”当天夜里,陶罐自动碎裂,那片叶子化作飞灰,随风而去。
孩子长大成人,成为第一位“沉默顾问”,游走于各国高层之间,不提建议,不说判断,只问一句:“你们准备好接受答案了吗?”许多人因此推迟决策,有些人甚至放弃追问。而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至于阿禾与音娘,始终未现踪迹。有人说他们在西域重建了愿听屋,只为倾听自愿倾诉者的心声;也有人说他们已化作风,常年盘桓于昆仑山巅,守护着那位白发老人的归途。
而沈知白,在一个寻常午后,坐在藤椅上读完了笔记的最后一行字。他合上书,抬头望天,看见燕子衔着桃花飞过屋檐。那只瘸腿的老狗趴在脚边,尾巴轻轻摇了两下,便再未动弹。
他笑了笑,摘下铜铃,轻轻放在石桌上。
铃未响。
风起了。
远处传来孩童嬉闹声,夹杂着一句清脆的童谣:
>“不说不怕,不听不伤,
>心若相知,何须声扬?”
夕阳西下,余晖洒满庭院。
那一瞬间,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低语。
却又无比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