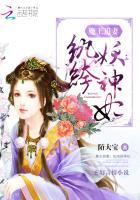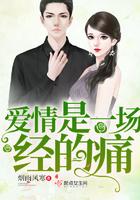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俗仙 > 390人煞不用修了(第1页)
390人煞不用修了(第1页)
陈乾六微微挠头,说了一句:“这许多人,却如何管理?”他虽然一手建立了大联盟,但日常都靠几个徒弟,自己并不管事儿。
吕三娘淡淡说道:“如今这些玄鲸岛的人已经奉我为主。”话音未落,陈乾六就感觉到了,。。。
雪融后的第三日,溪水涨得急了。
她清晨去岸边拾纸船时,发现水流比往常湍急许多,几乎将停泊在浅滩的船只尽数卷走。那些孩子们折的小船,有的被卡在石缝间挣扎晃动,有的已顺流而下,翻了个身,载着未读完的心事奔向未知。她蹲下身,伸手捞起一只半湿的船,展开后看见上面用蜡笔画了一个太阳,底下歪歪地写着:“我想爸爸回家。”字迹被水晕开,像一道泪痕。
少年从身后递来一块干布,默默接过纸船,轻轻吸去水分。他没说话,只是把那张纸摊平,压在随身携带的木匣下风处晾着。她望着他的侧脸,忽然觉得这七年里他瘦了许多??不是身形,而是眼神里的重量沉了下来,像是背负过太多未曾出口的歉意。
“你说,它们真能传到吗?”她终于开口,声音轻得仿佛怕惊扰水面的倒影。
“我不知道。”他低头看着自己映在水中的脸,“但有人写了,就说明还在相信。”
她笑了,指尖抚过唇角,却不自觉颤了一下。昨夜她又梦见第八塔崩塌的瞬间,母亲站在火光中回头望她,嘴唇开合,却没有声音。醒来时少年正坐在床边削一支桃枝,刀锋划过木纹,发出细微的沙响。那一刻她突然明白,有些话不必听见,也能懂。
午后,村中小学堂来了个陌生女人。
她穿着洗旧的灰布衣裳,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脚上的胶鞋裂了口,露出一角袜子。孩子们起初躲着她,直到她蹲下来,从包里掏出一叠泛黄的纸页,一页页铺在泥地上,笑着说:“这是你们写给溪水的话,我替你们找到了回音。”
她竟是沿江而上一路收集漂流信件的人。她说,在三百里外的渡口小镇,有个瞎眼的老邮差坚持每天打捞河面漂浮的纸片,晒干、整理、分类,再由她这样的“信使”分送各地。他们不识所有人名,也不知地址,只能凭着模糊的地貌描述和天气痕迹推测归属。“但我们知道,”女人说,“每一封信都曾被人郑重折好,放进水里,就像放走一颗心跳。”
孩子们围成一圈,争抢着辨认自己的笔迹。有人跳起来喊:“这是我写的!我说我想养只猫!”也有人突然红了眼眶,小声念出纸上别人写下的回应:“你不是孤单的,我也想妈妈。”
少年站在人群外,静静听着。他忽然转身走向桃林深处,挖出埋藏已久的铁盒??那是七年前他离开前亲手封存的,里面装着他写给她却从未寄出的三十六封信。每一封都只有寥寥数字,最长的一句是:“今天看见一朵云像你小时候扎的辫子,我站了很久。”
他抱着盒子回来,交给那女人:“麻烦你,也帮我送一次。”
女人接过,没问收件人是谁,只点头:“只要还有人在等,我们就一直走。”
当晚,暴雨突至。
雷声滚过山脊,闪电劈开夜幕,照亮整片桃林。新长出的紫花在风雨中微微颤抖,却始终挺立。她坐在屋内油灯下抄写《俗人守则》的新篇,写到一半,忽觉胸口闷痛,笔尖一顿,墨滴落在纸上,晕成一片深色花瓣。
少年察觉异样,立刻放下劈柴的斧头冲进来,扶她躺下。她的呼吸短促,手指冰凉,额上渗出冷汗。他慌了,连唤她名字数声才见她缓缓睁眼。
“没事……”她勉强笑了笑,“只是梦太重了,压住了心。”
他沉默片刻,忽然起身取出那支削好的桃枝,点燃一端,投入炉火之中。火焰腾起刹那,空气中弥漫开一股清甜香气,似有若无的童谣旋律随之浮现,如同有人在极远处哼唱。她闭目聆听,呼吸渐渐平稳。
“这是……‘听香’?”她轻声问。
他点头:“母亲教我的最后一课。她说,真正的倾听不在耳,而在气息之间。当两个人共有一缕烟、一口呼吸,哪怕不说一字,灵魂也能相认。”
她伸出手,与他十指交扣,感受着他掌心的温度慢慢渗入血脉。窗外雨势渐歇,屋檐滴水声如钟摆,丈量着时间之外的宁静。
次日清晨,第一批返乡者抵达村庄。
他们是曾在静默议会控制区生活多年的平民,多数曾接受过“情绪调节治疗”,面部表情僵硬,言语简洁如指令。可此刻,他们背着行囊站在村口,望着那棵新生的“言木”,竟有人无声落泪。
一位中年男子跪倒在树前,双手抚过地面,仿佛确认这不是幻觉。他喃喃道:“我记得……我女儿死前最后一句话是‘爸爸抱抱我’。我当时回答:‘情感依赖不利于灾后心理重建。’”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我现在……想学怎么抱人了。”
她迎上前,没有安慰,只是轻轻握住他的手。那一瞬,男人浑身一震,像是第一次感受到皮肤之间的温度传递。
越来越多的人陆续到来。有逃亡的医生、退役的安保人员、甚至一名前议会技术官。他们在溪边搭起临时帐篷,白天帮忙清理洪水留下的淤泥,夜晚围坐在篝火旁,轮流讲述过去不敢承认的记忆。有人说起自己曾亲手删除亲人遗言;有人坦白曾为晋升举报邻居“情感异常”;还有一个年轻女孩低声说:“我忘了我妹妹的样子,只记得她喜欢蓝色发绳……我烧了她所有东西,因为那是规定。”
没有人指责。只有倾听。
第三天夜里,她召集众人进入听学院旧堂。
火堆燃得旺盛,映照着墙上残存的古老铭文:“言为心声,默即失魂。”她站起身,声音不高,却穿透寂静:
“我们今晚不说忏悔,也不谈宽恕。我们只做一件事??找回名字。”
她拿出一本破旧的册子,是当年幸存者名录的手抄本。她翻开第一页,念道:“林小禾,七岁,失踪于冬至疏散行动。”然后停下,看向人群中一位佝偻的老妇人。
老人浑身一颤,颤巍巍站起来:“那是我孙女……我以为她死了……可昨夜,我在梦里听见她叫我‘奶奶’,声音那么清楚……”
“那就重新叫她一次。”她说。
老人闭上眼,泪水滑落:“小禾……奶奶在这里。”
全屋静默。片刻后,一个孩子模样的身影悄悄出现在门口,手里攥着一根蓝发绳,怯生生望着众人。没人知道她是何时来的,也没人追问真假??但在那一刻,所有人都选择相信她就是林小禾。
类似的场景接连上演。有人唤回了以为早已死去的母亲,有人终于喊出三十年未提的父亲姓名,更有一位失语多年的老兵,在众人齐声念出他战友名单后,忽然嘶哑开口:“我还记得你们每一个人的脸。”
黎明前,她独自走出大厅,来到溪边。
月光依旧洒在水面上,但今夜的纸船少了些,取而代之的是无数盏手工扎制的河灯。村民们用废旧铁皮剪出心形轮廓,中间点上蜡烛,写上名字或一句话,轻轻放入水中。灯火随波逐流,宛如星河倾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