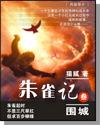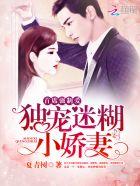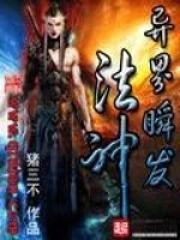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朱元璋的官,狗都不当 > 第二百一十三章 运河贯通(第2页)
第二百一十三章 运河贯通(第2页)
“好。”朱允?扶他起身,“从明日开始,你去实学馆旁听《建文新政史》《壬午忠烈传》《土地均平策》三课,每月考核一次。三年之内,若你能写出十篇心得,且每篇皆合民心之道,朕便信你。”
太子叩首再拜,泪洒青砖。
元宵节前夜,京城张灯结彩,街巷喧沸。然而戍卫森严,每一盏花灯下都有缇骑暗伏,每一座城门都设有铁蒺藜阵。百姓虽觉气氛异样,却仍欢庆如常??毕竟,这是三十多年来第一个可以公开谈论“建文”二字的元宵。
子时刚过,西城突发大火,烧毁民房十余间。火势一起,果然有人趁乱高呼:“建文复辟,诛杀篡党!”企图煽动暴乱。
但早已埋伏多时的新军营迅雷出击,仅用一刻钟便控制现场,擒获纵火者六人,皆身穿平民服饰,口音杂糅,身上搜出倭制短刃与火油瓶。
与此同时,南京方面急报:孝陵守军发现两名黑衣人试图撬开神道石碑,被巡逻队当场击毙,尸身检验后确认为日本忍者装扮,颈挂蒙古图腾护身符。
朱允?连夜召开军机会议,下令:“即刻公布审讯供词,将‘白翁’及其党羽罪证汇编成册,张贴全国。另命实学馆赶制《辨伪录》小册子,三日内发至各县学堂,让孩童都能识破谎言。”
此举极为高明。民间舆论迅速转向,原本对“靖难正义”尚存幻想者,见倭寇插手、外敌染指,顿觉羞耻。更有读书人撰文怒斥:“连外国人都想借我们祖宗之争渔利,可见所谓‘太宗正统’早已沦为笑柄!”
二月初八,朝廷正式宣布破获“双龙逆案”,斩首主犯十二人,流放协从八十六人。李维之削籍为民,其子押往云南充军。太子朱文奎亲自赴刑场观斩,面色惨白,却始终挺立不动。
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始知,仁政非软弱,而是以清明之心行雷霆之事。父皇不动声色而定乾坤,儿臣望尘莫及。”
风波稍歇,朱允?却未松懈。他知道,真正的战斗不在战场上,而在人心深处。
三月中旬,他颁布《史学令》:凡全国府县学塾,必须开设“建文历史课”,教材统一使用新版《明实录》与《靖难始末考》。教师须经实学馆培训考核,方可授课。学生年满十六岁,须通过“历史明辨试”,否则不得参加科举。
此举震动士林。一些老儒愤然抗议,称“改史乱纲”,甚至有国子监博士联名上书,请求保留“永乐盛世”章节。
朱允?召见诸生,只问一句:“你们教子弟忠君爱国,可若连谁是真君、谁是贼都分不清,谈何忠诚?”
众人哑然。
他又说:“朕不禁止你们研究永乐朝政绩。修长城、遣郑和、平漠北,皆可讲。但必须注明:此人得位不正,手段酷烈,废除仁政,屠戮忠良。功过分明,方为信史。”
最终,争议平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主动查阅旧档,撰写文章探讨“如果建文未亡,明朝会怎样”。甚至有学子提出“宪政雏形论”,认为建文年间推行的“廷议制”“言官独立”“赋税透明”已具近代政治萌芽。
春末,陆九渊带来另一项惊人发现:在凤阳地下暗道西侧三百步处,挖出一座密室,内藏数百卷竹简,经考证为洪武晚年太祖亲授方孝孺的《治国策要》手稿残篇。其中明确提出“设议会以集众智”“立法院以制皇权”“地方自治,中央监督”等理念。
朱允?捧读良久,泪落如雨。
“原来爷爷早就想过这些……”他喃喃道,“可惜,我当年太过年轻,未能深悟。若早十年施行,或许不必流亡半生。”
但他随即振作精神,召集实学馆全体学者,成立“制度设计局”,以《治国策要》为基础,结合当代国情,起草《大明宪纲草案》。
草案核心内容包括:
一、皇帝权力受《祖训》与《宪纲》双重约束;
二、设立“议政院”,由各地推选贤才组成,参与立法与财政审议;
三、重大决策须经三省会签,军机处不得独断;
四、百姓有权通过“直言台”上书批评朝政,任何人不得阻挠或报复。
消息传出,朝野哗然。保守派惊呼“颠覆祖制”,激进派则嫌改革太慢。唯有民间反应热烈,许多乡村自发组织“读宪会”,请塾师讲解条文。
朱允?对此只说一句:“制度如舟,载人亦覆人。唯有不断修补,才能驶向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