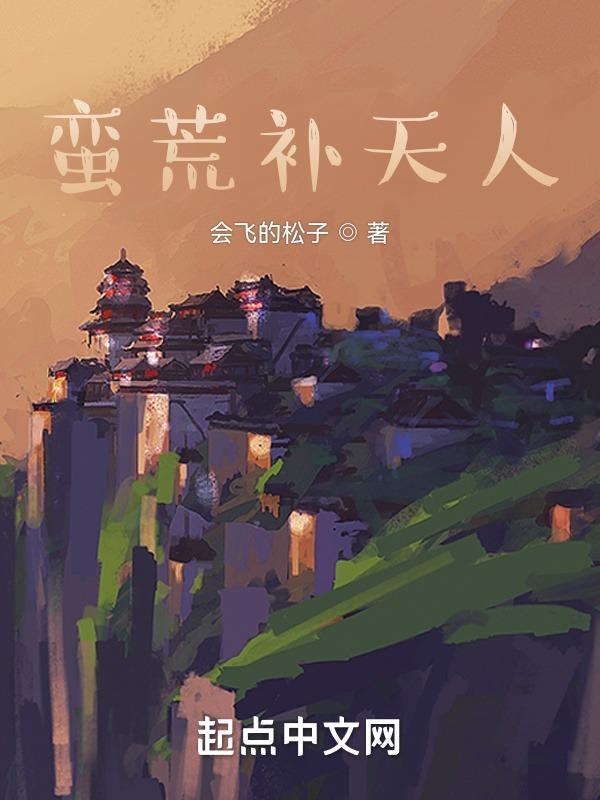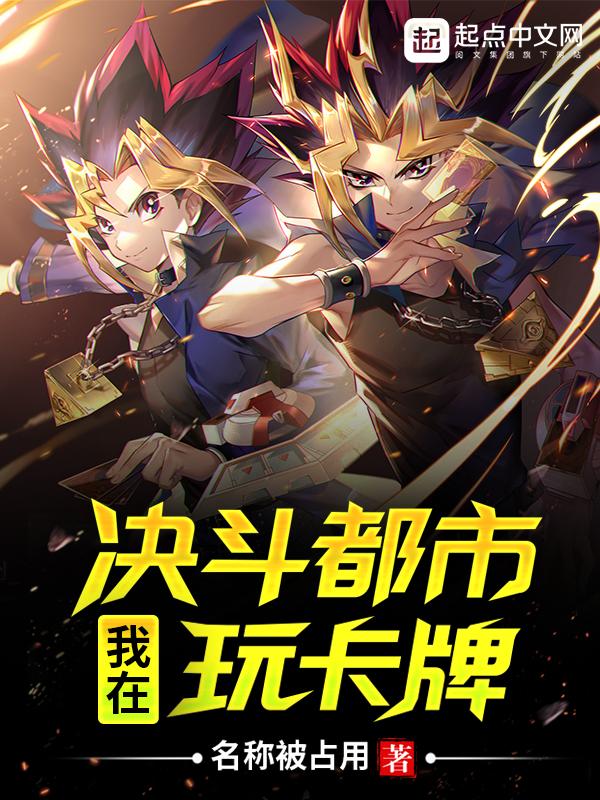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七零易孕娇娇女,馋哭绝嗣京少 > 第681章这么奇怪(第1页)
第681章这么奇怪(第1页)
正打算说几句安慰安慰江梦梦,就听到门被敲响了。
江远山去开的门,打开门发现是李广元他们,直接砰的一声,又把门关上了。
差点儿把李广元的脸拍扁。
李父李母见状还有些不高兴,这江家人也太过分了,说话的机会都不给。
本来江远山让他们直接滚蛋,结果李家人不依不饶,一直在外面废话。
没办法,还是把他们放了进来。
“你们来干什么?我妹还没把事情跟你们说清楚吗?我们家要退婚,反正也什么都没拿你们的,以后你们要是要点。。。。。。
晨光的手掌贴在锅盖边缘,感受着蒸汽从指缝间钻出的节奏。这温度他记得??三年前那个雪夜,他蜷缩在福利院后巷的纸箱里,梦见自己被一口大锅盛着,在沸水中翻滚。醒来时浑身发烫,却是因为有人把一床旧棉被裹在了他身上。第二天清晨,那名值班阿姨端来一碗热粥,碗底沉着两粒红枣。她不会手语,只是用勺子轻轻敲了敲碗沿,三下短、一下长,像极了现在蒸笼发出的闷响。
萨仁突然从酱缸旁直起身,鼻翼微动。她小跑过来,拽住晨光袖口,另一只手指向西边山梁。那里本该空无一物,可晨光眯起眼,竟看见一道灰影贴着坡地缓缓移动。他立刻吹响挂在脖子上的铜哨,三短一长??这是夜间警戒信号。
众人迅速集结。周振国取下墙角的巡逻棍,苏婉往保温桶里塞进几个刚出炉的馍,玛依莎则抱起医药箱。阿力牵来两匹老马,鞍鞯早已磨得发亮。林溪站在台阶上点了人数:“十六人留守,七人随行。”她说完顿了顿,“巴图,你留在屋里。”
老人没争辩,只将轮椅挪到记忆墙下,取出一块布开始擦拭勋章。那是李长根临终前亲手挂在他胸前的,上面刻着“支边模范”四个字,漆皮已斑驳。晨光路过时,看见他在唇语:**“去吧,火种不能断。”**
队伍迎着暮色出发。风刮得紧,枯草如针扎脸。行至半途,萨仁忽然翻身下马,跪在地上侧耳倾听。片刻后她猛地抬头,双手快速比划:**“地下有声音……很多人咳嗽。”**
周振国皱眉。这片荒坡曾是废弃矿道入口,六十年代塌方后就被封死了。可若真有人被困……他看向林溪,后者已抽出随身匕首,在冻土上划出简易地图。“先探通风口,”她用手语说,“晨光、萨仁跟我走,其余人在外围警戒。”
三人借着残月攀上岩壁。一处塌陷的石缝中,果然飘出微弱的人声。晨光摘下背包里的录音匣,贴在缝隙处开启收音模式。磁带缓缓转动,杂音之中渐渐浮现出断续的对话片段:
“……水……三天没喝了……”
“别睡……孩子还在喘气……”
“要是能吃口热的……哪怕一口……”
萨仁的眼眶瞬间红了。她扑上去用指甲抠挖碎石,指尖很快渗出血丝。晨光拦住她,从腰间解下振动仪??这是新研发的搜救设备,能通过地面传导声波频率判断生命体征。仪器嗡鸣三声,显示内部至少存活七人,其中包括两名儿童。
返回营地已是凌晨。巴图一直守在炉前,见他们回来立刻推近烤盘,上面温着姜汤和馍片。林溪一边喝一边召集紧急会议。苏婉提出拆解太阳能灶组件,组装便携式加热装置;玛依莎建议调配高热量糊剂,便于输送;阿力主动请缨带队破障,却被林溪否决。
“太危险,”她盯着地图摇头,“我们不是救援队,是厨房。救人的方式,得用我们的方法。”
天未亮,回声堂全员开工。面粉加驼奶粉、沙枣蜜调和,压制成易碎但耐储的应急饼;药材组连夜熬制清肺糖浆,装入小竹管密封;晨光带领聋哑学员制作“触觉导航绳”??每隔三十厘米缝一个不同形状的布结,盲人可通过抚摸辨识方向。
正午时分,第一套“生命餐包”完成。共二十份,每份包含两张热馍、一支药管、一根导引绳、一张盲文求生指南。最特别的是,每个餐包外都缠着一段细铁丝,末端系着一枚铜铃。只要轻摇,就会发出与回声堂开饭钟相同的音律。
“让他们听见希望。”晨光在纸上写道,递给摄像机镜头。
下午三点,突击队出发。这次由周振国领头,带着五名体力最好的成员,背负餐包与工具攀上矿道废墟。晨光坚持同行,被安排在后方指挥通讯。他坐在一块青石上,双手始终按在振动仪上,仿佛能通过大地感知队友心跳。
破入行动持续了四个小时。起初只能用铁钎一点点撬松石块,后来发现一条旧排水渠尚存通道,才得以推进。当第一束手电光照进深处洞穴时,所有人倒吸一口冷气??
十七个人挤在不足十平米的空间里,靠啃皮带维生。两个婴儿躺在大人臂弯中,嘴唇干裂如旱地。有个女人怀里抱着死婴,仍机械地哼着摇篮曲。而角落里坐着个穿灰夹克的男人,正用炭条在墙上写遗书。
苏婉冲上前打开保温桶,掰开一块馍送到最近那人嘴边。对方本能地闭紧牙关,直到闻到香气才颤抖着张口。那一瞬,眼泪顺着沟壑纵横的脸颊滑落,砸在馍上洇开一圈深痕。
“慢点……还有……”她哽咽着重复这句话,手却不停,一块接一块递出去。
与此同时,外面突然传来骚动。一辆军绿色吉普车疾驰而来,跳下几名穿制服的干部。为首者举着文件吼道:“谁允许你们擅自挖掘?这是危险区域!出了事谁负责?!”
林溪迎上去,平静出示县革委会特批函件。“我们没挖矿,”她说,“我们在送饭。”随即指向身后正在抬出伤员的队员,“这些人,是我们刚刚救出来的活人。”
对方愣住。这时,洞内传出一阵微弱却整齐的铃声。那是幸存者们摇响了餐包里的铜铃,一声声汇成潮水般的回应。
傍晚,所有获救者被送往县城医院。新闻纪录片摄制组连夜赶到,拍下了全过程。画面里,一个瘦脱形的老矿工握着萨仁的手不放,嘴里反复念叨:“香……真香啊……像我妈做的……”
当晚,回声堂灯火通明。不仅是为庆生,更为追思。他们在院中立起一块木碑,刻上“忘名者之食”五个字。下面埋了一只陶罐,里面封存着今日使用过的全部厨具残片,以及一张合影??十九位成员并肩而立,中间空着的位置写着“未归之人”。
巴图让人取来那张泛黄的全家福,轻轻覆在碑面。照片上年轻的蒙古母亲抱着婴孩,笑容温润如春水。他摩挲良久,忽然转向林溪:“明天,我想教萨仁做奶豆腐。”
林溪怔了怔,点头。她知道,那是草原上母亲传给女儿的第一道食物。
翌日清晨,阳光洒满院子。巴图坐在轮椅上,面前摆着铜锅、纱布与新鲜羊奶。萨仁跪坐一旁,神情庄重如受戒。晨光负责记录整个过程,用盲文记下每一滴凝结的时间。
“火要小,”巴图用手语慢慢解释,“心也要静。奶液沸腾不是结束,是开始。你要听它说话,看它流泪,等它自己愿意变成另一种模样。”
萨仁专注地看着乳白液体在锅中缓缓涌动,气泡破裂时溅起细小泪珠。当絮状沉淀浮现,她伸手试温,却被烫得缩回。巴图笑了,用自己的手覆上去,引导她再次探入。
“疼吗?”他比划着。
女孩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