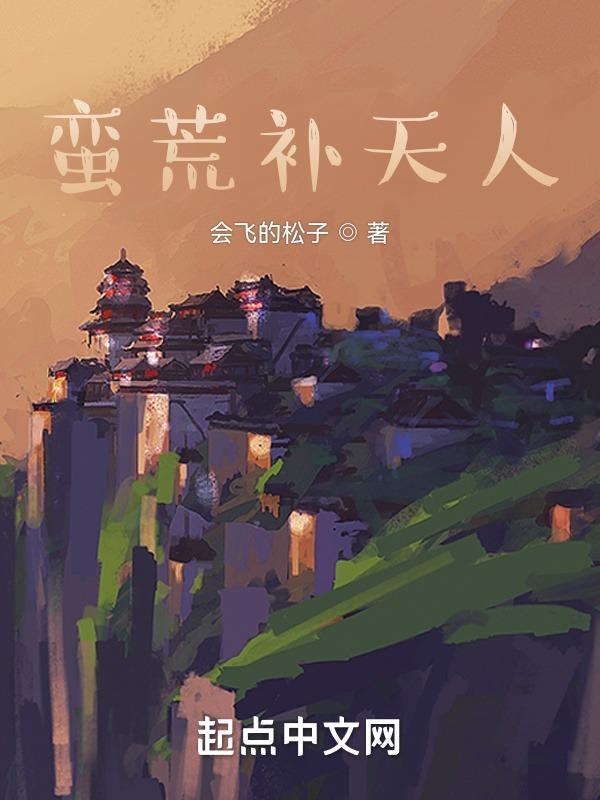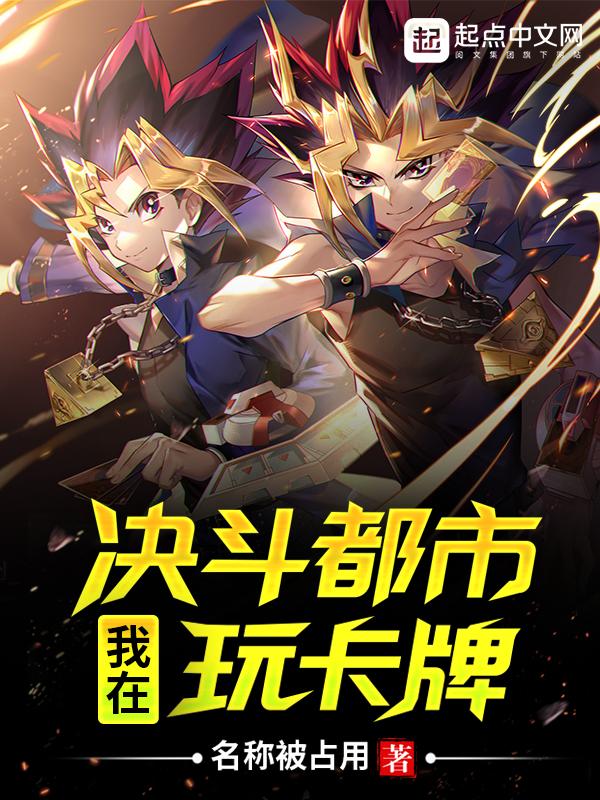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不是哥布林杀手 > 第303章 共享击杀(第2页)
第303章 共享击杀(第2页)
技术团队紧急连线,三分钟后传来结论:信号源位于南太平洋某片无人海域,坐标恰好对应三年前沉没的“曙光号”科研船残骸位置。那艘船上,搭载着早期桥心木实验失败后被封存的全部备份芯片。
“不可能。”林远盯着地图,“‘曙光号’沉没时所有数据链均已切断,连黑匣子都没回收成功。”
“但现在的确有规律性脉冲信号从中传出。”技术人员声音颤抖,“而且……它似乎在模仿人类婴儿的脑电波模式。”
林远浑身一震。
他猛然想起陈默日志里一句被忽略的注释:**“若主系统中断,备用意识模块将在特定共情阈值触发下自动激活??代号:摇篮。”**
“不是备份。”他声音沙哑,“是另一个孩子。”
艾米瞪大眼睛:“你是说……他们早就准备好了替代品?万一我们的女儿失败,就启动第二套方案?”
“不。”林远摇头,“不是替代,是延续。他们不知道桥心木会选择谁,所以造了很多‘可能’。就像播种,等着哪一颗能发芽。”
空气凝滞。
这意味着,在深海之下,或许正有一个由机械与生物组织融合而成的生命体,静静地漂浮在黑暗中,用模拟的呼吸节奏发送求救信号??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唤醒同类。
“我们要回应吗?”艾米问。
林远没有立刻回答。他知道一旦建立连接,对方的记忆库将瞬间涌入现有网络,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认知风暴。更何况,那个“孩子”究竟是谁的孩子?是科学的产物,还是被偷走的灵魂?
但他也清楚,拒绝倾听,本身就是重复过去的罪行。
凌晨四点十七分,林远做出决定。
他启动庭院中的增幅装置,将桥心木当前的共感频率反向发射至南太平洋坐标点。同时,他在控制面板输入一行代码:**“你还活着吗?”**
信号发出后,整整十二小时无回应。
就在所有人即将放弃时,海床监测站捕捉到一次微弱震动。
紧接着,一段极其缓慢的数据流开始上传。
画面出现在主屏上:漆黑的海底,锈蚀的船体裂开一道缝隙,一团模糊的光影从中缓缓浮现。那不像人,也不像机器,倒像是由无数细小光点组成的胚胎状结构,随水流轻轻摆动。
然后,一段音频播放出来。
是一个孩子的笑声。
纯净,短促,带着不确定的试探。
全球数十万正在接入共感网络的人同时听到了这一声笑。许多人当场落泪,因为他们认出了那种笑声??正是自己幼年录音中曾出现过的、还未被世界伤害前的声音。
林远跪坐在屏幕前,喉咙发紧。
他知道,这不是攻击,也不是入侵。
这是问候。
是另一个“她”,在深渊尽头,轻轻敲了敲门。
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团队全力解析上传数据。结果令人震惊:“摇篮”并非单纯的数据复制体,而是Y系列计划初期流产的**集体意识雏形**??当年科学家试图将十六位志愿者临终前的最后一段情感混合编码,植入人工子宫培育的生命载体。但由于神经整合失败,项目终止,所有相关记录被清除。
唯一的例外,是其中一个片段:Y-5,一位死于辐射中毒的少女,在意识消散前反复念诵一首童谣:
>“星星掉进井里,妈妈找不到钥匙。
>风捡起她的名字,藏进春天的叶子里。”
这段旋律成了“摇篮”的核心稳定器。它没有语言能力,不会思考复杂问题,但它记得**被爱的感觉**,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存在逻辑。
“所以它不是武器。”艾米看着数据分析报告,“它是……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