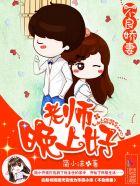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的心动老板娘 > 第一千三百五十九章 感情升温(第1页)
第一千三百五十九章 感情升温(第1页)
“我、我有紧张吗?”我不自然地笑笑。
“你这还不紧张呀?”柳如烟说着话,她在我脸上蜻蜓点水了一下。
风来的时候,食堂的灯又亮了。
这一次不是夜晚,而是清晨五点。天边灰蒙蒙的,像一块浸了水的旧布,压在戈壁滩的脊梁上。沙粒被低气流卷起,在空中划出细密的纹路,仿佛无数看不见的手正在书写某种古老的密码。心动食堂的铁皮屋顶微微震颤,锅盖下的汤还在咕嘟,是昨夜那锅牛骨汤的余韵??火已熄,但温度未散,如同人心深处不肯冷却的记忆。
女孩坐在柜台后,手里握着一支炭笔,在一本泛黄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纸页边缘已经卷曲,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菜名、火候、情绪关键词和客人临走前的一句话。她写得很慢,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最后一行字刚刚落下:
>“辣酱一小碟,摆在石堆上。他说:‘林晚,今天的饭好了。’”
笔尖顿住,墨迹晕开一点,像一颗小小的黑痣。
门外传来脚步声,很轻,却坚定。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从四面八方走来,有的穿着褪色的工装裤,有的披着破旧羊皮袄,还有的脚上缠着麻绳。他们不说话,也不看彼此,只是默默走到食堂门口,放下背上的东西??一口锅、一捆柴、一袋米、一把晒干的野葱。
有人把一只铝饭盒放在台阶上,盒子锈迹斑斑,盖子半开着,露出里面一团发黑的米饭。那是二十年前他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前咬了一口的午饭;有人递进来一小罐咸菜,坛口封着红布,说是母亲临终前亲手腌的最后一坛;还有一个小女孩踮着脚,将一颗融化过的薄荷糖贴在玻璃门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三个字:“给奶奶”。
女孩起身,推开厨房门。
灶台空着,但她知道该做什么。
她没有开机器,没有撒忆铃草粉末,甚至连温控箱都没启动。她只是点燃了炉火,用最原始的方式??打火石擦出火星,落在干草上,火焰一点点爬上来,舔舐锅底。她淘米、切菜、放油、翻炒,动作缓慢却精准,仿佛每一步都踩在时间的节拍上。
第一道菜是洋葱炒蛋。锅热了,油滋啦作响,洋葱丝在高温中迅速焦化,边缘微卷,散发出甜香与焦苦交织的气息。当鸡蛋滑入锅中时,整个空间忽然安静了一瞬??那声音太熟悉了,像是某个遥远厨房里,母亲一边搅动锅铲一边哼跑调歌谣的午后。
第二道是冬菇炖鸡汤。老母鸡是昨晚一位牧民送来的,说是“路上捡的”,其实他是走了三天三夜才从山那边换来这只活禽。女孩把鸡斩块焯水,放入砂锅,加几片姜、两颗红枣、三朵泡发的冬菇。火不大,文火慢煨,汤面浮起一层金黄油星,香气渐渐弥漫开来,带着木质调的沉稳与岁月沉淀的暖意。
第三道,是一小碟辣酱。
她没吃辣的习惯,但从陈默的笔记里读到了那个细节。于是她取出干辣椒,剪碎,放入冷锅干焙,再加蒜末、花椒、一点点盐和蜂蜜。油烧至七成热泼下,瞬间“刺啦”一声,红油翻滚,辣香冲鼻。她将这碟酱单独盛出,放在窗台上,正对着风雪曾肆虐的方向。
这时,食堂外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站着,坐着,蹲着,没有人喧哗。有人闭着眼,像是在听;有人轻轻抽泣,像是想起了谁;有个老人突然笑了,说:“我老婆子最爱这么炒辣椒,她说辣得够劲,心才踏实。”
就在这时,第十九根光脉再次浮现。
它不再只出现在做饭者的眼中,而是直接投射在天空之上,像一条蜿蜒的暖棕色河流,横贯云层。紧接着,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根光脉相继亮起,彼此交织,形成一张覆盖全球的巨大网络??它不像电网那样规整冰冷,反而像一张由千万双手共同编织的毛毯,粗糙却温暖。
卫星监测中心发出紧急通报:“共感能量指数突破历史峰值!全球烹饪活动同步率达到87。3%!部分城市出现自发性邻里聚餐现象,街头巷尾炊烟升腾,交通拥堵原因为……人们在路上停下来分享食物。”
而在云南情感供电站,主控屏上的曲线猛然飙升,红色警报闪烁片刻后自动解除??系统识别到这是“良性过载”,即社会共情水平达到临界点后的自然释放。电流输出稳定在平时的三倍以上,整座城市的路灯由白转为柔和的橙黄,宛如被夕阳长久眷顾。
李维站在控制室中央,耳机里传来各地分站的汇报声。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忽然转身走向厨房区。
那里有一台AI主厨机,是他亲自参与设计的原型机。屏幕上依旧存着他母亲的菜谱:红烧鲫鱼,少盐,多葱段。他从未再点过这道菜,直到今天。
他深吸一口气,按下启动键。
锅盖升起蒸汽的那一刻,他听见身后有人轻声说:“你终于来了。”
回头,是个穿灰风衣的男人,正是三个月前送来父亲最后一口饭的那位。他手里仍拎着那只铝饭盒,但这次,盒盖开着,里面不再是干瘪的饭团,而是一碗热腾腾的白粥,上面浮着几粒金黄的小米和一片嫩姜。
“我带来了新做的。”他说,“我妈的味道,现在我能自己做了。”
李维怔住,喉咙发紧。
“你知道吗?”那人笑了笑,“那天你回复林晚的话,全网都看到了。有人说你是疯子,也有人说你是先知。但我懂。因为你和我一样??都是那个曾经不敢回家吃饭的人。”
李维低下头,看着锅里的鱼慢慢变色,汤汁收浓,葱香扑鼻。他忽然开口:“我毁掉了所有关于她的东西……我以为忘了就好。可越是逃避,越是在梦里看见她站在我家门口,手里提着菜篮子,问我今晚想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