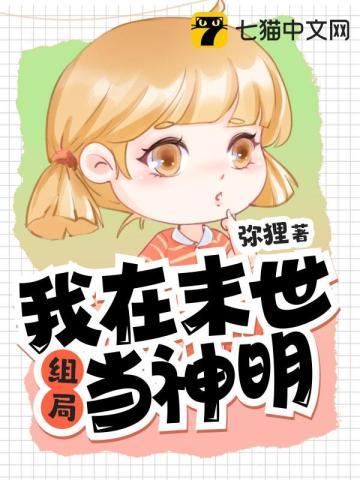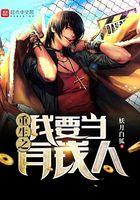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独享卡池 > 第299章 回归与奇怪的小队成员(第2页)
第299章 回归与奇怪的小队成员(第2页)
“我们得去。”我说,“不是因为责任,是因为……我们听到了。”
列车缓缓减速,前方出现一座荒废的站点,站名牌歪斜地挂着,字迹模糊,依稀可辨“青梧”二字。门开时,冷风灌入,带着腐叶与铁锈的气息。我们下车,身后车门关闭,列车无声驶离,消失在隧道深处。
夜雨未歇。
街道空无一人,两旁建筑破败不堪,藤蔓攀爬在墙体裂缝间,像一道道愈合失败的伤疤。远处,那座医院矗立在山丘之上,轮廓阴森,唯有三楼一扇窗户透出微弱的光??不是电灯,更像是蜡烛摇曳的火苗。
我们步行上山,泥泞湿滑,每一步都像踩在记忆的边界上。
抵达医院门口时,铁门半塌,锈迹斑斑。门柱上刻着几个几乎被风雨磨平的小字:“愿言皆得回应”。
我怔住。
这句话,我在笔记本第十二条规则末尾写过。
不是抄袭,是呼应。
我们推开残门,步入大厅。地板塌陷多处,天花板漏水,滴答声与呼吸机的节律惊人相似。墙上贴着褪色的病历卡,照片中的人眼神空洞,嘴角却带着诡异的微笑。
“他们在笑。”陈萤轻声道,“可他们一句话都说不出。”
“也许正因如此,他们的笑才更真实。”我说,“那是对沉默最倔强的反抗。”
我们沿楼梯向上,每一步都激起尘埃飞扬。三楼走廊尽头,那扇透光的房门虚掩着。
推开门,屋内陈设简陋:一张病床,一把椅子,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封信,信封泛黄,写着“致未来读此信之人”。床头点着一支蜡烛,火光摇曳,映照出墙上密密麻麻的刻痕??全是同一句话,用不同字体、不同深浅反复书写:
>**轮到我了。轮到我了。轮到我了。**
床上躺着一位老人,瘦骨嶙峋,戴着呼吸机面罩,胸膛微弱起伏。他的右手垂在床边,指尖沾着炭灰,似乎曾用力在地上划写什么。
林远舟蹲下查看,地面残留的痕迹拼出两个字:“救……我。”
“他还活着。”陈萤握住老人的手,声音发颤,“而且他一直在等。”
我拿起那封信,打开,里面只有一张纸,字迹工整却透着疲惫:
>亲爱的陌生人:
>
>如果你读到这封信,说明“声音网络”再次启动了。我是第七号观察者,也是最后一名守夜人。我们曾是医生、护士、家属、志愿者,自愿进入静默状态,以维持卡池底层协议的稳定。我们的语言能力被主动封锁,作为交换,我们成为记忆的锚点,防止所有被讲述的故事彻底消散。
>
>但现在,锚即将断裂。
>
>其他人已相继沉睡,意识归于寂静。我是最后一个还能感知外界的人。我请求你,复述这封信的内容。不必署名,不必传播,只需让这三个字再次响起:
>
>**轮到我了。**
>
>这不是告别,是交接。
>
>当你说出它时,我就不再是唯一的守夜人。
>
>而你,将成为下一个倾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