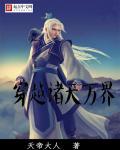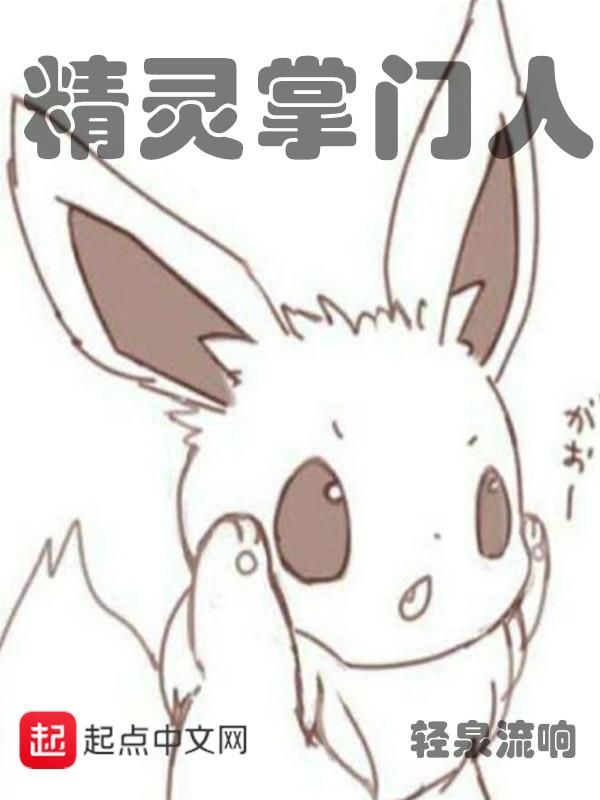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斗罗:龙王之太极玄真 > 第二百四十二章 玄真大帝扶墙而出传灵塔易名前夕世纪之变4K(第1页)
第二百四十二章 玄真大帝扶墙而出传灵塔易名前夕世纪之变4K(第1页)
一夜无眠。
淡白的阳光从厚重的窗帘缝隙里挤了进来,却丝毫没有冲散房间内的靡靡气息。
空气温暖炽热,弥漫着暖昧甜香,绯红旖旎仍在继续。
气质冷艳高贵的御姐老师,此刻牢牢占据主导,镇压着。。。
石屑簌簌落下,像一场微型的雪。林小愿的手指被划破,血珠渗出,滴在无字之书的第一页上,瞬间被吸收,仿佛那纸页是活的。她没有停下,继续刻下第二个字:“听。”我听??不是听见声音,而是听见沉默背后的挣扎,听见罪孽深处那一丝颤抖的悔意。
风从地底裂缝中升起,带着远古尘埃的气息,卷动她散落的发丝。那本无字之书缓缓翻开,每一页都开始浮现文字,不是她写的,也不是任何人执笔,而是由这片土地的记忆自行书写。一个个名字浮现:曾投票决定他人死亡的学生、执行“情感净化”的教师、默许暴行的旁观者……他们的忏悔以不同的字体、不同的语言、甚至不同的时间顺序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混乱却真实的图景。
林小愿盘膝而坐,将碎裂的竹笛残片拢在怀中。七节断骨般的竹片,仍微微发烫。她知道,这不只是乐器的损毁,而是一种蜕变的代价??当共鸣触及灵魂最深的阴影,载体便无法承受纯粹的重量。可她并不悲伤。笛子碎了,但她的心音还在,她的声音还在。
她抬头望向夜空。那里没有星辰,只有一层灰蒙蒙的光晕,像是集体记忆在自我遮蔽。这颗小行星名为“讳星”,存在于所有文明共同回避的角落。它不记录受害者的眼泪,而是收容加害者的良知??那些不愿面对、不敢承认、甚至已被遗忘的“我曾伤害过你”。
歌声再度响起,这一次不再是道歉,而是一段叙述:
>“你说那天阳光很好,
>你说投票只是程序,
>你说淘汰的是‘情绪不稳定者’,
>可你知道吗?
>那个被选中的孩子,
>昨晚还借你半块橡皮。”
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石子投入死水,激起一圈圈涟漪。地面再次震动,更多的石像从沙中浮现,面容模糊,姿态各异??有的低头跪拜,有的双手掩面,有的张嘴欲言却无声。它们是无数个“我本可以阻止”的化身,是千万次沉默积累成的负罪之形。
第九天的黎明,第一缕光照进裂缝时,一名老者踉跄走出阴影。他穿着早已被淘汰的“选择课”制服,胸前别着一枚锈迹斑斑的徽章。他的嘴唇干裂,声音几乎不成调:
“我是……课程设计者之一。”
他停顿了很久,像是在与某种无形的锁链搏斗。
“我们教孩子们用逻辑判断谁该留下,谁该离开。我们说……这是为了群体最优解。”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跪下,额头触地。
“可最优解里,从来没有眼泪的位置。”
林小愿静静地看着他,没有上前搀扶,也没有回应。她只是轻轻哼起一段旋律??那是她在七岁那年吹错的第一个音,走调得离谱,却始终记得。老人听着听着,肩膀开始颤抖,然后是压抑的呜咽,最后变成嚎啕大哭。那哭声惊起了藏匿于岩缝中的几只盲鸟,扑棱棱飞向天际,划破了百年未变的寂静。
就在此刻,无字之书自动翻页,新的篇章浮现标题:《加害者的声音》。
林小愿知道,这才是最难的一章。人们愿意倾听受害者,因为同情是安全的;人们也愿意赞美觉醒者,因为希望令人安心。但加害者呢?他们的话语常被视为辩解,他们的泪水被认为是软弱的表演。可若连他们都不被允许发声,赎罪又从何谈起?
她站起身,走向下一尊石像。
“告诉我,”她说,“你最后一次说‘对不起’,是在什么时候?”
石像没有回答,但它的表面开始渗出暗红色的液体,像血,又像锈。林小愿伸手触摸,指尖传来一阵刺痛,随即脑海中闪过画面:一个少年站在教室中央,全班举手表决是否将他逐出社群。他看着最好的朋友犹豫了一下,然后缓缓举起手。那一票,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就是那个朋友?”她轻声问。
石像微微点头。
“后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