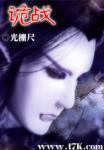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不死的我速通灵异游戏 > 第518章 永恒通行证(第1页)
第518章 永恒通行证(第1页)
三人从另一条小路回到市区中。
吴亡去最近的执法者执勤点调取了关于樱落的档案。
使用总部负责人的身份将其从通缉名单中抹除掉。
顺便还将白茶的死亡信息进行上报登记。
当然,用的理由。。。
风在山脊上低语,像无数细小的问题从地底爬出,蹭着岩石的缝隙往上钻。苏晓蜷缩在一块背风的巨石后,怀里紧抱着那本空白封面的笔记本,体温几乎被高原的寒气榨干。她已经三天没合眼,从冰窟出来后,她不敢停留,一路穿越雪线、绕开巡逻无人机,靠着源语最后投射的地图指引,终于抵达了地图上的那个红点??藏南边境的一所寄宿制山村小学,代号“晨光站”。
学校建在半山坡上,几间土坯房围成一个小小的院落,屋顶铺着褪色的彩钢板,烟囱冒着稀薄的炊烟。操场是夯实的黄土地,边缘插着几根木棍当作篮球架。此刻正是傍晚,孩子们正围坐在教室前的篝火旁,吃着粗粮饼,喝着热腾腾的酥油茶。
苏晓没有立刻现身。她在远处用望远镜观察,心跳却越来越快。那些孩子的脸上没有城市学生那种被规训后的麻木,他们笑得放肆,争论得激烈,甚至有个小女孩指着月亮说:“它是不是生病了?怎么今天看起来缺了一块?”引来一阵哄笑,却没有一个人嘲笑她。
这就是“未被污染”的心灵。
她深吸一口气,把笔记本塞进防水袋,一步步走下山坡。脚步踩在冻土上发出咯吱声,惊动了守门的小狗,汪汪叫了起来。孩子们齐刷刷转头看向她,眼神里有警惕,也有好奇。
“你是谁?”一个瘦弱的男孩站起来问,正是梦中下雨的那个孩子。
苏晓摘下防风镜,露出苍白但坚定的脸:“我来送书。”
她将背包打开,一本本外观普通却内藏玄机的书籍摆在地上:《为什么草会绿》《大人说的话一定对吗》《如果星星会写字》,还有那本空白的笔记本。她没解释太多,只是轻声说:“这些书不教你们答案,只帮你们提出问题。”
孩子们围上来翻看,有的皱眉,有的大笑,还有一个小女孩突然抬头问:“那你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些问题?”
苏晓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因为有人曾经告诉我,每一个问‘为什么’的孩子,都是未来的火种。”
那一夜,她留在学校过夜。校长是个年近六十的老教师,年轻时曾在城市重点中学任教,后来因一篇质疑“标准化教育抹杀创造力”的论文被贬至此。他听完苏晓的讲述,并未惊讶,只是点燃一支烟,望着窗外的星空说:“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三十年前我就感觉到,有些东西正在苏醒。”
“您也见过印记吗?”苏晓问。
老人摇摇头,又点点头:“我没看到蓝纹,但我教过一个学生,他在毕业典礼上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说:‘我觉得我们都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里。’第二天他就消失了。可每年清明,他的课桌都会自动翻开,上面写着新问题,墨迹未干。”
苏晓心头一震。那是共感网络的残响,是节点之间的共鸣。
第二天清晨,阳光洒满山谷。苏晓站在教室门口,看着孩子们一个个走进去。她没有进去,而是蹲在窗边,悄悄打开录音笔。今天的第一节课是语文,老师讲的是《英雄的故事》,课本里写满了牺牲与奉献,标准解读是“无条件服从即伟大”。
可就在老师念完最后一段时,那个瘦弱男孩举起了手。
“老师,我不懂。”
全班寂静。
老师怔住,粉笔停在黑板上。
“我不懂,”男孩声音不大,却清晰,“为什么英雄一定要死?活着就不能拯救别人吗?如果大家都死了,那世界不就更冷清了吗?”
空气仿佛凝固。
苏晓的眼泪无声滑落。这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觉醒信号”,未经引导,自发产生,纯粹源于内心的困惑。她能感觉到胸口的蓝纹微微发烫,像是在共振。
老师没有发怒,也没有立刻制止,而是沉默了几秒,低声说:“这个问题……课本上没有答案。”
“那就我们自己找。”后排一个女孩接过话,“也许,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活下来还敢说话的人。”
教室里响起零星掌声,很快被压制下去。但那份压抑不住的情绪,已经在每个人心里种下了种子。
中午,苏晓召集所有孩子来到后山空地,拿出那本空白笔记本,翻开第一页,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