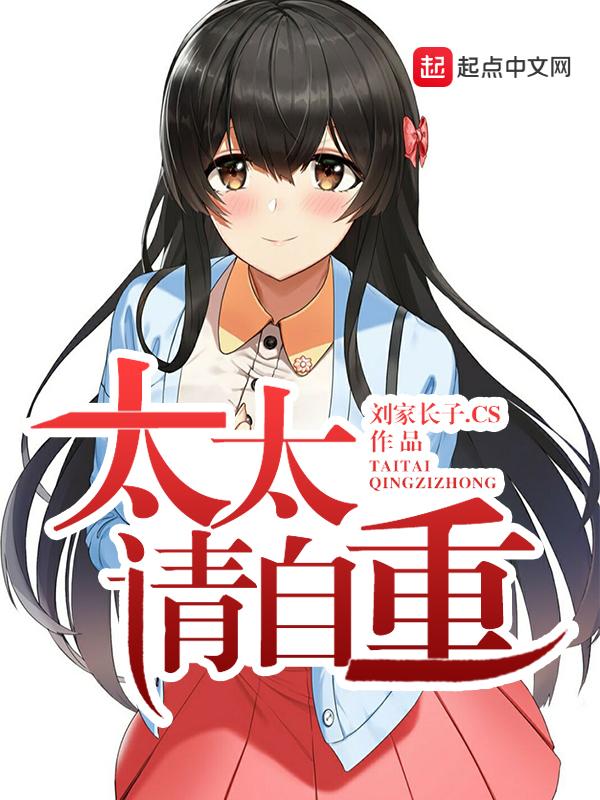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二婚嫁京圈大佬,渣前夫疯了 > 第1551章 我会对小十好的(第2页)
第1551章 我会对小十好的(第2页)
小满缓缓走上台阶,脚步轻柔。当她踏上最高一级时,系统自动触发了一段音频:
>“我是小满。今天我说出了第一个完整的句子:‘我想回家。’”
那是她七岁时的声音,沙哑、断续,却坚定得像刀刻进石头。
她闭上眼,把手贴在胸口,仿佛能听见十年前那个小小的身体里,心脏如何一次次撞向命运的墙。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的脚步声。
她回头,看见山果气喘吁吁地爬上坡,手里紧紧攥着什么东西。
“姐姐!”她扑过来,摊开手掌??是一只折得不太整齐的纸鸟,翅膀有些歪,但用心涂上了金粉。
“我学了好久才学会。”她仰着脸,眼睛亮晶晶的,“你说过,纸鸟能带走黑暗。”
小满怔住,眼底泛起水光。她接过纸鸟,小心翼翼放进胸前口袋,然后蹲下来,认真打出一串手语:
**谢谢你,把我留在光明里。**
山果似懂非懂,却用力抱住她。
夕阳西下,两个身影依偎在山顶,背后是整座城市的灯火渐次点亮,如同万千颗回应的心跳。
当晚,沈知远接到教育部来电,对方语气郑重:“‘回声行动’已被纳入‘十四五’特殊教育创新试点项目,中央财政将拨款支持建设十所区域性感知教育中心。首选址建议放在西南山区??那里有大量留守儿童和残障儿童长期处于教育真空。”
挂掉电话后,他翻开小满的“未来计划”本子,发现最新一页写着:
>**想去大山里的学校。**
>
>**那里的孩子,也许比我更久没听过掌声。**
他沉默良久,提笔在旁边写下一行字:
**我们可以一起建一所学校。不叫基地,也不叫机构。就叫“回声小学”。**
三天后,周维衡如期而至。
那天天气晴好,校园里新栽的樱花树抽出嫩芽。他穿着朴素的灰西装,身后跟着四位年龄不等的孩子,最小的不过五岁,戴着助听器,眼神怯生生的;最大的十二岁,全程用手语与母亲交流。
沈知远亲自迎接,陈婉端来茶水,气氛起初有些拘谨。
直到小满出现。
她安静地走来,蹲在孩子们面前,先是对着最小的女孩笑了笑,然后慢慢举起双手,打出一段温柔的手语:
**你好呀。我以前也不会说话,也不敢看人。但现在,我可以教你折一只会飞的纸鸟。**
女孩睁大眼睛,犹豫片刻,竟也笨拙地模仿着抬起手,比出一个歪歪扭扭的“好”。
那一刻,周维衡站在人群后方,忽然红了眼眶。
他原以为自己是为了验证而来,为了学术反思而来,可当他看到这群孩子眼中重新燃起的光,才明白??这不是一场实验,而是一次救赎。
午后的阳光洒在操场上,小满耐心地教每个孩子折纸鸟。她动作极慢,一遍遍示范,用图画解释步骤,还会轻轻扶正他们的手指。
那位十二岁的男孩起初抗拒,低头不语。小满便坐到他身边,拿出素描本,画下两个小孩并肩站着,一个张嘴说话,一个用手比划,头顶飘着一行字:**我们都一样重要。**
男孩盯着画看了很久,终于伸手接过一张彩纸。
当最后一只纸鸟完成时,八个人站成一圈,同时将纸鸟抛向空中。
春风拂过,那些轻盈的翅膀在阳光下闪烁,像一群挣脱束缚的灵魂。
周维衡默默掏出手机,拍下这一幕。回去的路上,他写下一篇题为《论教育中的非典型胜利》的文章,公开发表于《心理学报》:
>“我们习惯以‘正常’为标准衡量成长,却忘了有些孩子生来就在逆风奔跑。他们不是缺陷者,而是开拓者??用触觉代替听觉,用视觉诠释旋律,用沉默讲述千言万语。”
>
>“小满不是一个奇迹。她是千万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实现。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复制她,而是创造能让所有‘不同’都被尊重的土壤。”
文章末尾,他附上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