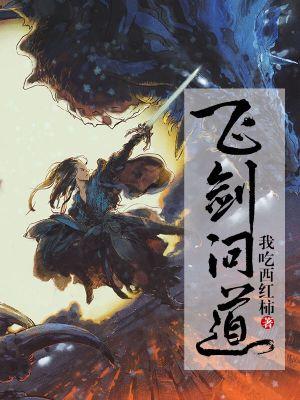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阎王下山 > 第2016章 将她抓来(第2页)
第2016章 将她抓来(第2页)
“这是她在最后一次共听活动中留下的。”赵哲说,“她没来得及送出。但我们一直替她守着。”
李山双手颤抖地接过照片,紧紧贴在胸口,仿佛要将它嵌进心脏。
那一夜,他留在了听见馆。
十八个孩子再次围坐成圈,蜡烛逐一燃起。轮到李山时,他站起身,声音哽咽:“我今天想对小禾说一句话……爸错了。爸不该让你一个人扛那么久。如果你还能听见,请原谅我这个笨拙的父亲……下辈子,换我来找你,换我先说‘我爱你’。”
话音落下,屋外忽然起风。
铜铃轻轻一晃,发出一声清响??不多不少,正好第八次。
众人屏息。
周默抬头望向天空,只见乌云散开,星光倾泻而下,第八颗星格外明亮,仿佛回应着某种跨越生死的呼唤。
第二天清晨,李山离开了山村。临行前,他将那枚银戒摘下,放进《回声》日记本中,并在扉页写下:
>“献给所有不敢开口的灵魂。
>我曾是堵住女儿嘴的那堵墙,
>今天,我选择拆掉它。”
赵哲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轻叹:“有些人走了十万八千里,只为找回一句该说却没说的话。”
周默问:“他会好吗?”
“我不知道。”赵哲微笑,“但我相信,当他某天梦见女儿笑着跑向他时,那不再是梦,而是他们之间重新建立的频率。”
日子一天天过去,听见馆的名声越传越远。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堆满了木桌,有的写着“我也想建一座听见馆”,有的只是简单一句“谢谢你让我知道,我不是怪物”。
然而,平静之下,暗流涌动。
某日黄昏,一辆黑色轿车悄然驶入山村,在村口停下。车门打开,下来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手持录音笔,胸前挂着媒体证件。他径直走向听见馆,敲响门扉。
“我是《都市观察报》记者林振邦。”他开门见山,“最近关于‘共听时刻’的报道铺天盖地,但我查到一些疑点??比如那份署名‘回声’的研究报告,根本无法追溯来源;联合国宣布设立‘全球共听日’的会议记录中,也并无此项提案的正式表决流程。请问,这一切究竟是真实的社会运动,还是精心策划的心理操控?”
周默皱眉:“你是在质疑这场共听的真实性?”
“我只是追求真相。”林振邦冷静道,“情感可以被引导,集体行为可以被煽动。我不否认你们帮助了许多人,但当一种理念被神化,就可能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强迫人们必须‘被治愈’,必须‘感恩’,必须‘放下’。那些依旧痛苦、依旧不愿说话的人呢?他们是否也被视为‘不合格的倾听者’?”
赵哲端茶走出,闻言微微一笑:“你说得没错。任何运动都有被滥用的风险。但我们从未宣称‘共听’是万能药。它只是提供一个空间,让沉默者有机会发声,让倾听者学会尊重。”
他顿了顿,目光深邃:“倒是你,林先生,为何如此执着于揭露‘真相’?你采访过多少真正参与共听的人?听过他们的故事吗?还是仅仅凭着数据和逻辑,就想否定千万人心底的真实感受?”
林振邦一怔。
“我母亲死于产后抑郁。”他低声说,“她生下弟弟后,整日流泪,说自己没用,是个坏妈妈。我爸骂她矫情,亲戚劝她‘想开点’,没人认真听她说过一句话。最后,她在浴室割腕,留下一张纸条:‘对不起,我还是没能变成你们想要的样子。’”
他的眼眶红了:“所以当我看到你们提倡‘倾听’,我既感动,又害怕。因为我怕这又是一场虚假的安慰,怕有人利用人们的伤痛牟利。”
赵哲点头:“你的怀疑,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倾听??你在听你自己内心的恐惧。”
他转身从书架取下一本旧册子,递给林振邦:“这是我母亲当年的心理档案复印件。医生诊断她‘情绪障碍’,建议药物治疗。但她真正需要的,不过是一个人肯蹲下来,握住她的手,说:‘你已经很好了,不必再拼命。’”
林振邦翻开档案,手指停在一页手写笔记上:
>“患者反复提及胎儿心跳声,称每晚都能听见。建议家属避免强化此类幻觉。”
他猛地合上本子,呼吸急促。
“你知道吗?”赵哲轻声道,“我母亲后来告诉我,她不是幻听。她是真的听见了。那个未出生的孩子,一直在用心跳对她说话。只是这个世界,不允许母亲哀悼一个未曾见面的生命。”
林振邦久久伫立,最终收起录音笔,深深鞠了一躬:“明天的报道……我会如实写下我听到的一切。”
他离开后,周默问:“你会让他发表吗?”
“当然。”赵哲望着远方,“真正的信念,经得起质疑。就像真正的爱,不怕暴露伤口。”
当晚,赵哲独自坐在老槐树下,翻阅《回声》日记本。一页页翻过,全是陌生人的告白:
>“我恨我妈,因为她宁愿救狗也不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