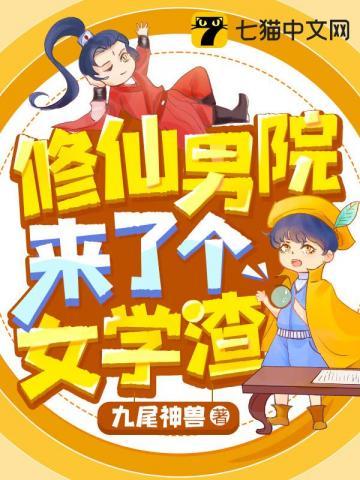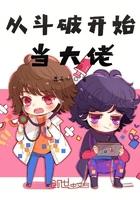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让你下山娶妻,不是让你震惊世界! > 第1643章 魂煞(第4页)
第1643章 魂煞(第4页)
安禾已不再年轻,眼角有了细纹,头发也染上霜色。她依旧每天记录“信号”,虽然再未收到完整信息,但偶尔,某朵花会在特定时刻发光,某片叶子会浮现短暂字迹,或是某阵风带来熟悉的气息。
她相信,那不是幻觉。
那是**频率的回信**。
这一年春分,她带着学生们来到花园,准备举行年度仪式??点燃七盏灯,象征七次告别与七次重逢。
就在她举起火种的刹那,天空忽然暗了下来。
不是乌云,而是一群候鸟。
它们排成螺旋状,盘旋于心冢上空,叫声清越,竟隐隐合着一段旋律??正是那首童谣的变奏。
学生们惊呼抬头。
安禾却笑了。
她放下火种,静静仰望。
鸟群飞过七次,最后一次,其中一只脱离队列,俯冲而下,落在她肩头。
那是一只蓝羽山雀,喙边带着一道浅浅白痕,像是一道旧伤。
它歪头看了她一眼,忽然开口,声音稚嫩却清晰:
“姐姐,我们替他看了很多春天。”
说完,振翅而去。
安禾站在原地,泪如雨下。
她知道,这不是结束。
这只是另一种开始。
***
多年后,一位年轻的记者来到云坪村,采访关于“听语奇迹”的传说。
他走访村民,查阅资料,最终在一本泛黄的校刊上,读到一篇学生作文,标题是:
《我见过的那个男人》
>“我没见过他。但我梦见他。
>梦里他在一片花田里走路,身后跟着好多孩子,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
>他走得很慢,时不时停下来,帮一个摔倒的男孩拍灰,给一个哭泣的女孩擦眼泪。
>我问他:‘你是谁?’
>他笑着说:‘我是那个答应下山娶妻的人。’
>我又问:‘那你娶了吗?’
>他望向远方,轻声说:‘我娶了人间风雨,嫁给了岁月长河。我的孩子,是每一个愿意倾听的心。’”
记者合上书页,久久无言。
临走前,他问安禾:“您觉得,他还会回来吗?”
老人坐在藤椅上,手中握着那支早已失效的录音器,目光投向花园。
七朵花正沐浴在夕阳中,轻轻摇曳。
“他从未离开。”她说,“只要还有人愿意为别人疼,他就一直在。”
风起,花动,铃兰低语,如诉如歌。
远处,不知谁家孩童哼起一支古老的山谣,调子模糊,却透着温暖。
像是回应,又像是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