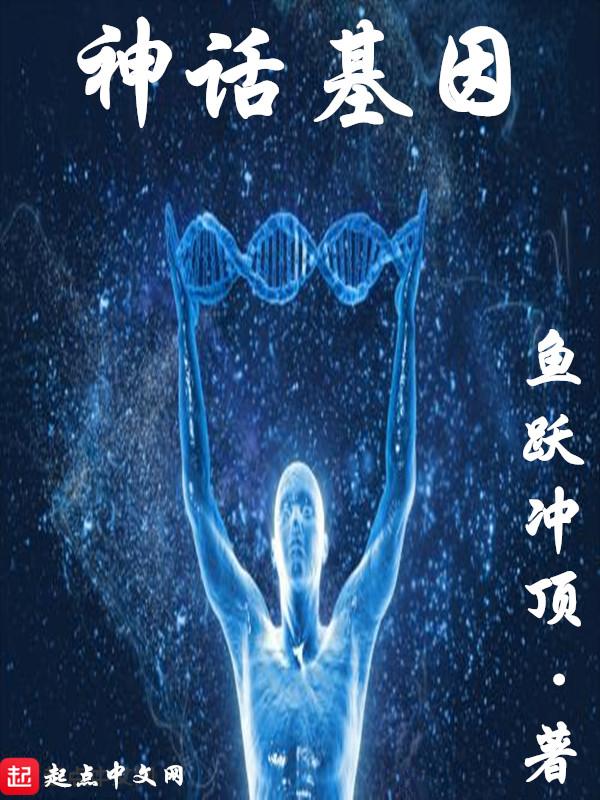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大明:哥,和尚没前途,咱造反吧 > 第一千二百八十六章 抖一回就抖到死(第1页)
第一千二百八十六章 抖一回就抖到死(第1页)
男人的眼皮抖了抖,忽然把布包往怀里一塞,转身就窜。
朱瀚甚至没抬手,脚尖一挑,“叮”的一声,一枚细薄的铜钱钉进门框,男人刚贴到门上,肩胛就像被蛇咬住,整个人在原地。
“开窗。”朱瀚道。
朱标一愣:“窗?”
“这屋子里有两扇窗,”朱瀚看也不看那男人,“一扇朝街,一扇朝井。朝街那扇,锁舌是旧的;朝井那扇,锁舌是新的。说明有人常从井那侧进出。
朱标走到朝井的窗前,果然看见新漆未干的木锁,边上还蹭着鞋印。他扭开锁,推窗,一股潮气扑面,井口边的青苔亮得发滑。
“看见了。”朱标低声。
“谁从这走?”朱瀚问那男人。
男人死咬着牙:“你们自己去问井。”
“好。”朱瀚点点头,“我问井。”
他把窗阖上,回过身来,看着那男人:“你卖“归魂’给谁?”
“我不??”
“给蓝玉的人?”朱瀚打断他,“还是给宫里的人?”
男人的喉头滚动了一下,不言。
“你以为我问的,是罗宣。”朱瀚慢慢道,“我问的不是他。我问?????蓝玉死前的那一刻,谁在他的鼻翼下抹了这一把。”
男人的瞳孔缩了一下,像被针刺中,立刻又放大:“你胡说。”
“他‘自缢”的绳子,勒痕不深。死后吊上去,绳子挂得再好,也不会有生时那种颈动脉暴的痕。”
朱瀚的声音像在数铁钉,“他死前被人做过手脚。你供的是药,不是刀。”
男人盯着他,盯了很久,像在看一只没见过的兽。然后,他忽然笑了。
“王爷,”他嘶哑着嗓子,“你在找“谁动的手?你其实要找的是‘谁敢动手”。这药。。。。。。这药我卖给谁,你真想听?”
“说。”
“卖给影司’。”
朱标眉心一跳:“影司?”
“宫里一个影子衙门。”男人舔了舔唇,“不是锦衣卫,不是东厂,不是任何人。看不见,摸不着,只有脚步。有时候,你会听见脚步停在你床前??你醒来,什么都不记得。”
“影司的头是谁?”沈麓问。
男人笑得像在咳:“谁看得见影子的头?”
“价谁给的?”朱瀚问。
“谁的影子,就谁给。”男人抬起眼皮,里面是一层不怕死的红,“不过??影子是活人,有时候也会丢魂。你说是不是?”
“你卖给了谁来取‘魂?”朱瀚把最后的门堵死。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喉头里挤出两个字:“吴震。”
屋里的灯忽地爆了一声,油花炸开,火苗歪了一下,立刻又直了。
朱标与沈麓对视一眼。那名字,他们昨日才目送着被押去午门????下无生。
“死人不会来买药。”朱标低声道。
“活着的时候买的。”男人耸耸肩,“他每回都只要半包,说“够了’,很省。后来有一回,他说不够,要整包??那回之后不过三天,监里就死了一个大人物。
“蓝玉。”沈麓吐出这两个字,空气里像被压了一块铁。
“我不认名。”男人笑,“我只认脚步。”
朱瀚盯着他:“今晚你说了这么多,明天你还想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