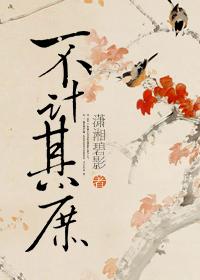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求求了,快回家练琴吧 > 568 命运的另一种投射(第2页)
568 命运的另一种投射(第2页)
***
湘西山村的清晨,雾气还未散尽。苗恒瑞又一次爬上后山,却发现老樟树下早已围满了孩子。他们每人手里拿着自制的“乐器”:竹筒、铁盆、木棍、空瓶子……
“老师!”扎辫子的小女孩蹦出来,“我们自己搞了个乐队!”
苗恒瑞惊讶地看着他们排成三列:第一列敲击节奏,第二列模仿自然声响,第三列负责即兴演唱。没有指挥,却出奇地和谐。
一曲终了,掌声雷动??来自他们自己。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练的?”苗恒瑞问。
“昨晚睡觉前。”一个男孩说,“我们发现,只要敢发出声音,就不会做噩梦了。”
苗恒瑞心头一震。
当天下午,村小召开家长会。原本预计到场率不足五成,结果几乎全员出席。家长们坐在一起,沉默地听着孩子们表演??一段由虫鸣、溪水、牛铃与童声合唱组成的十分钟即兴作品。
结束后,一位父亲站起来,声音沙哑:“我儿子以前总被说‘多动’‘不听话’。可刚才那一分钟,他敲的那个节奏……是我小时候放牛时常吹的山谣。”
另一位母亲抹着眼泪说:“我家丫头从来不敢大声说话,今天居然领唱了……她回家路上一直在哼。”
校长激动得说不出话,最后只憋出一句:“这课,必须继续开!”
苗恒瑞站在人群外,默默掏出笔记本,记下一句话:“教育的本质,不是消除差异,而是让每一种存在都能找到自己的频率。”
***
西南边陲的特殊教育学校里,马可迎来了第一批校外参观者??一群普通小学的师生。当他们走进“无声之声”展览厅时,所有人都戴上了感应手套。
灯光渐暗,地板开始震动。一组由听障儿童设计的节奏模式缓缓启动,配合着空中流动的彩色光波。孩子们通过手语引导节奏变化,每一次手势,都会引发环境反馈。
一名普通学校的孩子突然蹲下身子,把手贴在地上,眼泪无声滑落。
“他说……他第一次感觉到音乐是有形状的。”翻译老师哽咽道。
展览结束时,带队老师找到马可:“我们回去就要申请成为合作校。原来不是他们听不见,是我们一直没学会怎么‘听’他们。”
当晚,马可在日记中写道:“当我们拆除‘正常’与‘异常’之间的墙,世界才会真正响起完整的声音。”
***
张禹舟回到了最初的梦想起点??那所他曾就读的音乐附中。如今的教学楼焕然一新,琴房装了隔音棉,走廊挂满了获奖学生的照片。他在公告栏前驻足良久,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藏在十年前一场校际比赛的集体合影角落。
“张老师?”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传来。
他转身,是个戴眼镜的高一女生,手里抱着一本乐理笔记。
“您就是‘听见者’计划的发起人之一吗?”
他点头。
“我……我也想报名做志愿者。”她说,“我弟弟是自闭症患者,他不会说话,但从三岁起就会跟着音乐摇晃身体。我妈一直觉得那是怪癖,直到看了你们发布的《无声之声》视频,才明白那是他在表达。”
张禹舟看着她,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躲在琴房角落、渴望被理解的自己。
“你知道吗?”他轻声说,“有时候最勇敢的事,不是站上舞台,而是敢于承认??我也需要帮助。”
女孩用力点头。
临走时,她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抄写着一段旋律,并附言:“这是我弟弟唯一愿意重复听的一段音乐,是他自己哼出来的。您可以帮我看看,它有没有名字?”
张禹舟盯着那串音符看了很久。它简单、重复,却带着某种执拗的生命力。他忽然想起母亲心理咨询记录里的那句话:“如果时间能重来,我宁愿少赚一个月工资,也要坐在台下听他弹完那首《小星星》。”
他拨通黄楚贤的电话:“帮我联系一下技术组,我想做个声音转化程序??能把非标准哼唱转换成可演奏乐谱。”
“你要干嘛?”黄楚贤问。
“给一个孩子命名他的歌。”他说,“每个人都该知道,自己的声音,值得被记住。”
***
黄楚贤坐在办公室里,面前堆着上百份“百人守护者”的培训反馈表。她逐页翻阅,看到许多熟悉的句子:
>“我以为心理咨询只是倾听,现在才知道,倾听也可以是一种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