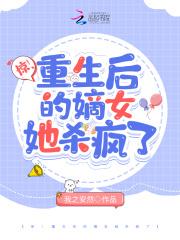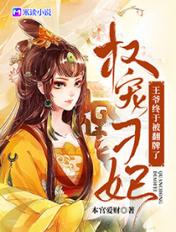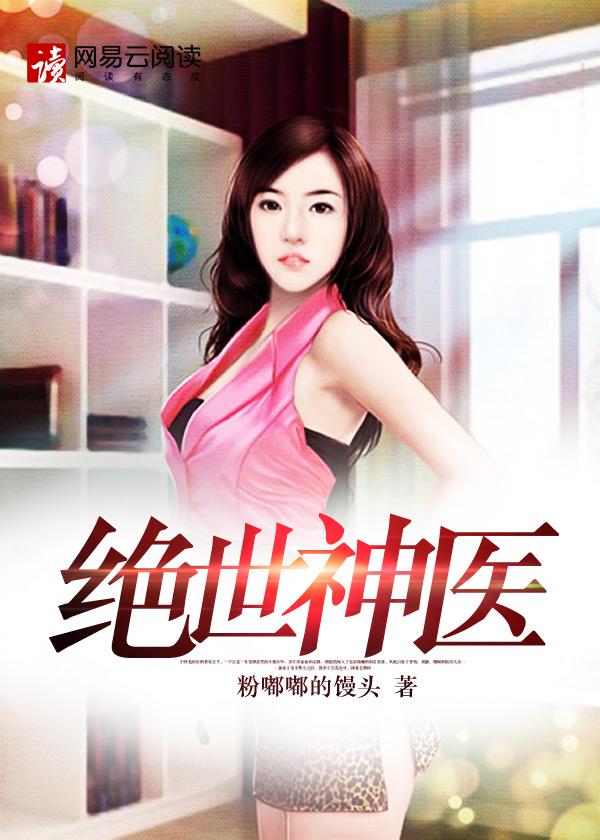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娘子天下第一 > 第七百零八章(第2页)
第七百零八章(第2页)
广播播出后,内蒙古一位牧民听众连夜骑马三十里,找到当地文化站站长,要求查阅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户籍档案。站长起初拒绝,但在听说“有个女人为这个死了”后,沉默良久,最终打开尘封多年的柜子,取出一本破旧登记簿,指着其中一页说:“你看,这里写着‘迁出’,其实是饿死了。我们当时都懂这个字的意思。”
类似的涟漪不断扩散。山东一位退休法官自发组织“民间陪审团”,邀请百名公众在线聆听“回声纪”档案,就“历史是否应被追责”进行模拟审判。投票结果显示,87%的人认为“国家应对系统性遗忘道歉”。广州一位年轻律师据此起草《历史正义倡议书》,征集到两万名签名,虽无法提交人大,但通过海外渠道发布,引发国际关注。
四月清明,柳明志接到一个视频通话请求。来电者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背景是一间简陋的农村堂屋。她颤抖着举起一块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满仓之灵位”,旁边摆着一碗米饭、一碟咸菜。
“我是满仓的姑姑。”她说,“我活到九十二岁,第一次敢把他名字摆出来。昨天晚上,我梦见他了,还是那么小,穿着破棉袄,问我:‘姐姐,有人念我吗?’我说:‘念了,全国都在念。’他就笑了,然后消失了。”
通话结束前,她深深鞠躬:“谢谢你,让我儿子……不,我侄儿,终于回家了。”
柳明志久久无法言语。他想起母亲手稿中的另一句话:“记忆是亡者的归途。”如今,这条路正在被一点点照亮。
五月,他收到一封来自监狱系统的匿名信,称有一名服刑人员愿提供关键信息,条件是“确保其家人安全”。经多方验证,此人确系当年参与销毁母亲手稿的基层干事之一。他在狱中忏悔,交出了一份秘密笔记,详细记录了1983年专项行动中被查禁的书籍名录,其中包括《地方实录》原稿的销毁时间、地点及执行人姓名。
柳明志将这份笔记加密存档,并附上一句话:“我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让‘被迫沉默’成为历史。”他深知,真正的胜利不是扳倒某个人,而是让下一代不再需要恐惧地说真话。
夏至那天,“回声纪”迎来创立十周年。尽管国内无法访问,全球各地却自发举办了二十三场纪念活动。柏林一场展览展出了一百支“种子计划”钢笔,每支笔旁附一张照片:一个普通人手持钢笔,背后写着“我愿意记住”。纽约某社区中心放映了《他们不说,但他们活着》,放映结束后,全场起立默哀三分钟。最动人的是东京一所高中,学生们排演话剧《满仓》,谢幕时,全体演员齐声喊出那个名字,观众席中,一位华侨老人泣不成声:“我舅舅也叫满仓,死在河南老家。”
柳明志没有参加任何活动。他独自回到晋南老宅,在地窖原址立了一块石碑,上书:“此处曾藏真相,今归于风。”然后,他取出一支全新的钢笔,笔身刻着一行小字:“给下一个说话的人。”
临行前,他在村口遇见小宇的爷爷。老人拄着拐杖,背更驼了,但眼神清明。
“我孙子昨天学会写‘历史’两个字了。”他说,“他问我,爷爷,历史是什么?我说,历史就是不让好人白白死去。他又问,那坏人呢?我说,坏人也不该被忘记,因为他们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好人。”
柳明志点点头,将那支刻字钢笔递给他:“请交给小宇。告诉他,轮到他了。”
老人接过笔,郑重地揣进怀里,像接过某种圣物。
回程途中,手机再次震动。**【新上传】用户“黄河边老船工”分享音频《摆渡人》**
内容:1960年春,他曾用小船运送饿殍过河安葬,每具尸体脚下放一块石头防止漂回。某夜,发现一具女尸怀中仍有体温,婴儿尚存一口气。他冒险救活,取名“渡生”。六十年后,渡生成为医生,每年清明都随他回河滩祭拜无名者。
柳明志点开音频,苍老的嗓音在耳边响起:“那时候,死人比活人多。可只要还有一个心跳,我就得划桨。”
他闭上眼,轻声跟读:“只要还有一个心跳,我就得划桨。”
然后,他打开录音功能,将自己的声音录下:
>“我听见了。
>我记住了。
>我会传下去。”
点击上传,标签为#你说#我听#薪火相传。
他知道,这场漫长的传递远未结束。也许有一天,所有的声音都将沉寂,也许所有的努力终将被抹去。但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倾听,还有一个人敢于开口,那道微光就不会熄灭。
就像母亲在手稿末尾写的那样:
>“纵使黑夜漫长,
>只要有人记得黎明的模样,
>黎明就从未真正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