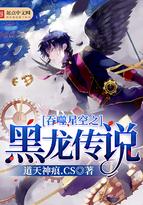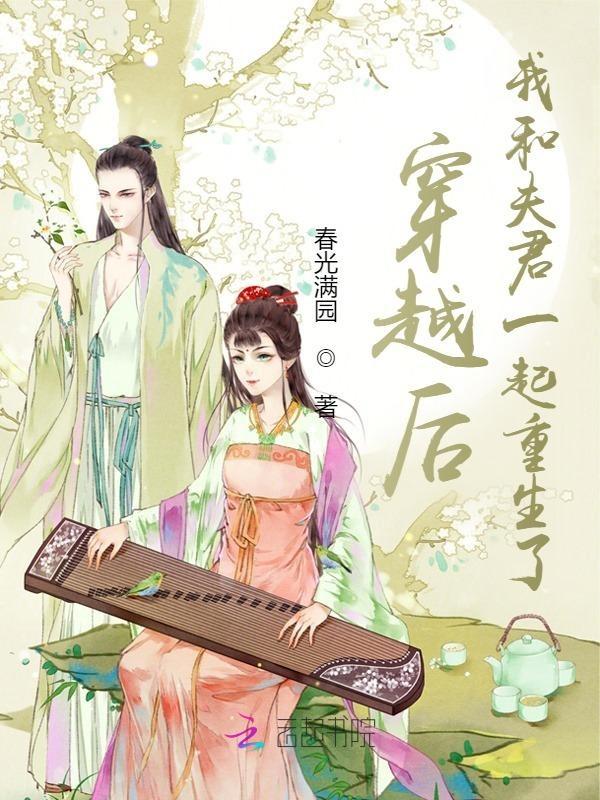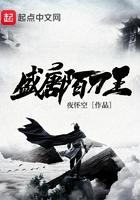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神话版三国 > 第四千八百三十章 大封群臣(第3页)
第四千八百三十章 大封群臣(第3页)
>“我们在此安息。
>不求复仇,只求知晓:
>后人是否还记得我们曾存在?”
探险队带回一块碎片,经破译确认,属于公元前四世纪某个消失的海洋文明。更令人震撼的是,DNA分析表明,部分遗骸基因序列与现存人类高度重合,说明这个族群并未彻底灭绝,而是被历史选择性遗忘。
策仁得知后长叹:“原来‘静语’不是现代发明。它是人类古老恐惧的回声,一代代重复上演。”
扎西则下令启动“跨纪元记忆桥接计划”,将这一发现纳入《本应活着的人》展区,并新增一条导语:
>“遗忘不止发生在昨天。
>它早已渗透进千年的黑夜。
>但我们今夜点亮灯火,
>不仅为照亮近处的伤痕,
>更要告诉远古的幽灵:
>我们来了。
>我们听见了。
>我们不会让你们再等千年。”
多年过去,地球的文明面貌已然不同。城市不再以征服命名街道,而是用“讲述者”、“守忆人”、“光莲使者”来纪念那些推动记忆复苏的灵魂。孩子们入学第一课不再是背诵国歌,而是学习如何真诚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那个曾带来图画书的小男孩,如今已是青年教师。他的课堂仍在继续,只是规模越来越大。每年春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齐聚阿婆树下,围坐一圈,轮流分享生命中最难启齿的真实。
有一年,轮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兵。他颤抖着开口:
“我年轻时奉命枪杀了一个孕妇。她说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没取名。我……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的眼睛。我不求原谅,只想让他知道??如果他还活着,我会教他骑自行车,带他去看海。”
全场寂静。片刻后,一颗晶果从树顶坠落,正好落在他掌心。果实裂开,流出一道柔光,映出一个模糊孩童的身影,朝他伸出手,嘴角微扬。
老人嚎啕大哭。
而在遥远星空中,那本横跨银河的巨书持续接收信号。外星文明或许尚未回应,但地球的广播从未停止。每一段故事都被编码成光脉冲,送往宇宙深处,像是一封永不寄出却始终坚持投递的家书。
某日清晨,策仁再次登上阿婆树顶端。他抚摸着那枚名为“希望”的晶果,轻声问道:“你说,我们真的能终结遗忘吗?”
风穿过树叶,带来万千低语:
>“只要还有人在讲述,
>就永远不会彻底遗忘。”
雨又落了下来,洗刷着大地,也滋润着新生的记忆。玻璃窗上的水痕再次汇聚成字,这一次,不再只是提醒,而是邀请:
>“轮到你了。
>轮到你了。
>轮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