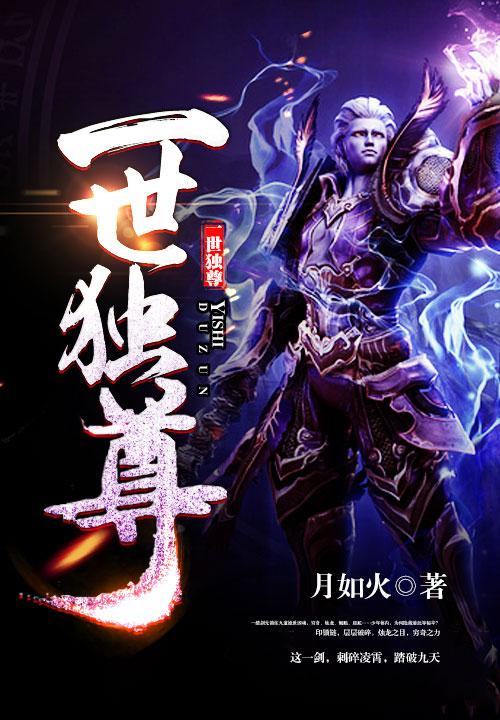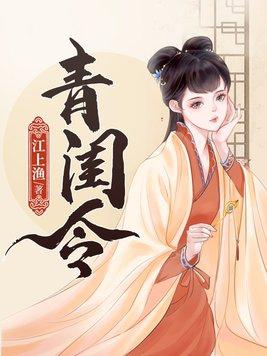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外科教父 > 1254章 乡愁(第1页)
1254章 乡愁(第1页)
一间堆满书籍和文献的办公室里,
梁教授枯坐在宽大的办公椅里,他脸上的皱纹沟壑纵横,眼中隐含一丝难以化开的复杂情绪,手机在手掌里已经握得温热
张春泉,那是他倾注了最多心血的学生啊!
曾经,在这间办公室里,他们为了一个实验数据争得面红耳赤;在无数个深夜里,他们一起守着仪器,等待那可能改变一切的结果;他手把手地教他设计课题,引导他思考科学的边界,甚至在他生活困窘时,悄悄用自己的津
贴补贴他。在他心中,春泉不仅仅是学生,更像是他学术生命的延续,是他未竟理想的寄托。他曾经那样笃定,这个天赋卓绝,又肯吃苦的年轻人,必将青出于蓝,成为撑起中国医学领域未来的栋梁。
张春泉出国的那天,梁教授亲自送他上飞机,临分别时,他握住张春泉的手: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学成后一定回来。
可最终,张春泉选择了大洋彼岸的那个顶尖实验室,一去不返。
起初还有几封邮件往来,语气恭敬却日渐疏离,后来,便彻底断了音讯。梁教授理解那边有更好的平台,更优越的条件,但理解不代表不心痛。那感觉,如同自己精心培育、视若珍宝的幼苗,被人连根拔起,移植到了异国的
土地上,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连一句挽留的话,都显得苍白无力。
上一次见面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张春泉登门拜访,梁教授起初心里颇为兴奋,可是话里话外,张春泉的意思要梁教授帮忙牵线搭桥接触杨平,希望可以与杨平合作的时候。梁教授心里明白,他这次来不是拜访恩师,而是
另有所指:他是带着任务来的。
“送客。。。。。。”那时的梁教授如同冰水淋心,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
那一声送客,他不知道心里有多痛,自从以后两人再也没有任何联系。
。。。。。。再试一次,再做最后一次努力,为了破壁计划。。。。。。
他的手指颤抖着,划过温热的屏幕,点亮。那个烂熟于心的国际长途号码,他从未存进通讯录,却早已刻在了心底。他的拇指悬在绿色的拨号键上方,几乎能感受到那虚拟按键的触感。
只要按下去,只要按下去。。。。。。也许就能听到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他该说什么?以老师的身份命令?还是。。。。。。仅仅以一个思念徒弟的老人身份,轻声问一句:“春泉,你还好吗?累了,就回来吧。。。。。。”
他的心剧烈地抽痛起来,混杂着多年未愈的失落、难以言喻的心疼,以及一丝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怕被再次拒绝的畏惧。他仿佛已经听到了电话那头礼貌却疏远的回应,看到了那次对话可能带来的、更深切的失望。
那根承载了万千思绪和沉重期望的手指,在空中僵持了许久,最终,还是无力地垂落下来。屏幕的光亮,因长时间无人操作而悄然熄灭。
他终究还是没有拨出这个电话。
有些伤口结痂了,就不要再轻易撕开。有些期望,破碎了,就让它埋在心底吧。
他长长地,无声地叹了一口气,将那部息屏的手机,轻轻推到了桌子的最角落,仿佛这样,就能将那份翻江倒海的情绪,也一并封存起来。
只是那挺直了一辈子的脊梁,在灯影下,竟显得有些佝偻了。
麻省理工白头生物实验室在全球享有盛誉,张春泉教授是实验室的联席主任之一,他年仅三十八岁,却已是领域内公认的顶尖学者,头顶着无数青年科学家梦寐以求的荣誉光环。
然而,他的内心却远不如窗外的景色那般宁静。
年轻的陈潇那番话在他脑海回荡缭绕,久久不能散去。
桌上摊开的几份中文科学新闻,头版头条都是关于“破壁”计划的报道。那些熟悉的地名,那些激昂的语句,像一根根无形的针,刺入他内心最深处不愿触碰的角落。
“春泉啊,你的天赋是我见过最好的,送你去美国,是希望你能学到最前沿的东西,将来回来,能够把中国的生物医学工程搞上去!”当年机场送别时,恩师拍着他肩膀的殷切目光,至今历历在目。
恩师将他视若己出、倾囊相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