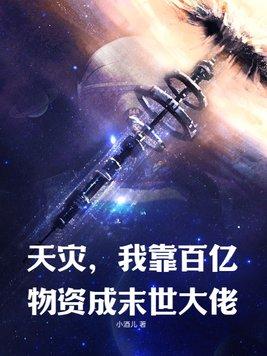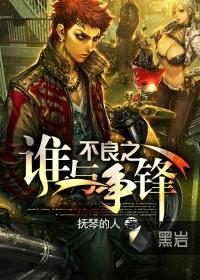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都重生了谁考公务员啊 > 第699章sweet姐的圆满(第2页)
第699章sweet姐的圆满(第2页)
压力之下,当地教育局终于松口,同意将该夜读班纳入“社区教育试点项目”,提供部分经费支持,并派遣在职教师轮流支教。
胜利虽小,却意义深远。
三个月后,“一万封家书”结集成册,命名为《光的足迹》。出版社主动联系免费印刷十万册,送往全国图书馆、乡村学校、社区中心。令人动容的是,许多读者读完后自发在书页空白处写下自己的故事,再把它放回公共书架,形成一本不断生长的“活书”。
而在西北某县城,一位曾举报“传播未经审核技术方案”的基层干部,在读完马强的成长日记后,主动联系平台,请求为当地牧民开设“智慧牧羊培训课”。他在信中写道:“我当初拦的是‘风险’,但现在明白,真正的风险,是让孩子一辈子只能放羊。”
春天再次来临。
平台用户突破一千五百万人,日均活跃超百万。越来越多的专业机构主动寻求合作:协和医院开设“家庭健康顾问”系列课程,中科院科学家录制《给农民的科学课》,甚至连国家图书馆也接入系统,开放百万册电子古籍供全民免费阅读。
变化不仅发生在数字世界。
山东那位成为“数字辅导员”的老人,如今已被县老年大学聘为客座讲师。他带着一群同龄人组建了“银发共学团”,每周直播一次“老年人防诈骗实战演练”。有一次,他模拟骗子电话,故意设下陷阱,结果台下七十多岁的大妈们一个个冷静拆招,最后齐声喊出:“你这是违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十二条!”全场爆笑,弹幕刷屏:“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而在青海玉树,卓玛老师带领学生们建起了“高原共学合作社”。他们用学到的电商知识,把手工编织的藏毯挂上网店销售,收入全部用于购买教材和教学设备。孩子们轮流当主播,用汉语和藏语介绍产品,直播间标题写着:“我们不卖贫穷,我们卖希望。”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连一些曾经持怀疑态度的公务员也开始悄悄使用平台。一位南方某市的科级干部匿名留言:“每天下班后学两节经济学课,半年下来,写材料思路清晰多了。局长问我是不是报了MBA,我说,我只是不想被淘汰。”
陈着看到这条时,忍不住笑了。
他知道,这个时代正在发生某种深层迁移??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成了普通人对抗命运的工具;学习也不再是功利的跳板,而是一种生存的尊严。
夏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次专题听证会。这一次,受邀发言的不再只是受益者,还包括曾经的反对者。那位撰写《知识平权背后的陷阱》的“资深教育观察员”坦诚道:“我曾以为你们是在挑战秩序,后来才发现,你们是在修复断裂。真正的教育,不该只存在于围墙之内,它应该像空气一样,无差别地滋养每一寸土地。”
掌声经久不息。
会后,教育部牵头成立“社会学习协同治理委员会”,邀请平台代表、民间讲师、用户代表共同参与政策制定。陈着作为成员之一,在会议上提出一项建议:“设立‘民间教育豁免清单’,明确哪些内容属于公民自主学习范畴,不受行政审批限制。比如识字、算术、生活技能、应急救护等基础能力,应视为基本人权的一部分,无需许可即可传播。”
提案获得通过。
那天晚上,他独自走在江边。晚风拂面,灯火倒映在水中,如星河流淌。手机响起,是林小雨发来的视频链接。点开后,画面出现在甘肃一个偏远牧场:马强正蹲在地上,调试新装的智能项圈。一只小羊脖子上戴着设备,屏幕上实时显示体温、心率和活动轨迹。父亲站在旁边,满脸骄傲。
镜头转向远处,十几个孩子围坐在一块太阳能供电的显示屏前,正在上一节数学直播课。黑板上写着今天的课题:《如何用函数预测草场承载量》。
马强对着镜头说:“叔叔,你说的知识,真的能让羊吃饱,也能让我们上学。”
陈着闭上眼,深吸一口气。
他知道,这条路还很长。某些地方仍在抵制,某些审查依旧严苛,某些声音仍在警告“不能放任自流”。但他也清楚,火种一旦点燃,风越大,烧得越旺。
年底,平台迎来第五个生日。没有庆典,没有宣传,只在首页更新了一句标语:
>“你学的每一分钟,都在改写中国的未来。”
而在后台数据库深处,那个被置顶的笔记依然静静躺着:
>“老师说重生是电视剧里的事。可我觉得,当我第一次听懂英语听力的时候,我就重生了。
>原来我不是笨,只是没人告诉我怎么学。
>现在我知道了,只要不停下来,每一天都可以重新开始。”
陈着又一次点开搜索框,输入“重生”。
跳出来的,已是成千上万条相似的笔记。
有人写:“我四十五岁考下电工证那天,觉得自己活过来了。”
有人写:“我妈五十岁学会用微信视频,看见外孙喊她‘奶奶’,哭了整整半小时。”
还有人写:“我在戒毒所学完了高中课程,出去那天,我要报名高考。这不是逆袭,是我终于敢面对自己。”
他一条条看下去,直到凌晨。
最后,他在自己的账号下写下一行字:
>“所谓重生,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从此刻开始,相信未来可期。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说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