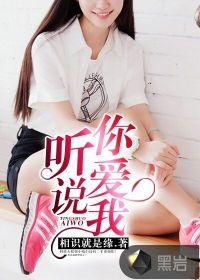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在现代留过学 > 第一千零八十二章 直把谅州作汴州(第1页)
第一千零八十二章 直把谅州作汴州(第1页)
当前,大宋朝廷在交州的统治,实行的双轨制。
既土客分治之法。
土司们在各自的领地,实行高度自治,以习惯法和传统治理。
安南都护府作为所有土司的最高上级和管理者。
无论是土司的袭。。。
雪后初霁,山间晨雾如纱。阿禾沿着旧道缓行,脚踩在积雪上发出细碎声响,仿佛踏着岁月的残页。他肩上的药箱早已换了模样,外皮斑驳,铜扣锈蚀,却依旧结实??这是赵砚当年亲手为他打造的,内有夹层三处,藏过密信、账册、甚至一册用蝇头小楷写就的《忆堂殉难录》。如今它盛着笔墨、纸张与几味草药,成了行走的书斋。
行至山腰,忽闻犬吠声起,一户人家柴门轻启,走出个裹着粗布棉袄的老妇,提着竹篮往田埂去。她抬头见人,愣了一瞬,随即放下篮子,颤声道:“是你……井边摇铃的先生?”
阿禾驻足,微笑点头。
老妇快步上前,从怀中掏出一本用蓝布包好的册子,封面墨迹已泛黄,写着“太行哭录?卷一”。“我记了三年,”她说,“从我爹讲起,讲到我儿子死在矿洞那年。一共七十二人,名字我都列了。”她声音低沉,却字字清晰,“他们不该连块碑都没有。”
阿禾双手接过,郑重地收入箱中。他知道这本薄册背后是多少个夜晚的辗转反侧,多少次对着空屋喃喃自语,只为不错过一个名字、一句遗言。他轻声道:“您写的,会传下去。”
老妇摇头:“我不图传不传。我就怕忘了。一忘,就像他们没活过。”
这话如针,刺入心腑。阿禾久久无言,只将一枚刻着“记得”的铜铃递给她:“若您愿意,可在这村设一口‘言泉’。孩子识字了,就让他们抄一遍,念一遍。一代代念下去,便不会断。”
老妇接过铃铛,捧在掌心,像接住一个沉甸甸的托付。
正午时分,阿禾抵达一处废弃驿站,原是元代所建,砖木倾颓,唯有一口古井尚存。井栏上爬满青苔,却被擦拭得干净,显有人常来。他在井边坐下,取出干粮啃食,忽听远处传来马蹄声急。
三人骑马而来,皆着商旅服饰,为首者翻身下马,摘帽行礼:“阿禾先生,川井七派我等前来接应。苏井三已在湖南联络十七县书塾,准备合编《楚南痛史》,急需您前去主持体例。”那人从怀中取出一封密函,以蜂蜡封缄,印痕为七井叠纹。
阿禾拆信阅毕,眉头微蹙。信中提及,甘兰进虽已伏法,其党羽仍有暗流涌动,近日频频收买地方文人,试图以“补遗”之名篡改民间史录。更有甚者,某些州县竟出现“反忆堂”组织,公然焚烧口述抄本,称“追忆旧事乃煽动民心”,已有两名传声童子被毒杀于途中。
他沉默良久,终将信投入火堆烧尽。
“告诉苏井三,我即刻动身。但请他转告各地主坛:从此以后,所有《未删国史》副本必须三份异地藏匿,不得集中;传声童子出行须两人同行,路线随机更替;每月底,各井盟须以暗语向邻坛确认安否,若三日无讯,即视为失联。”
使者领命而去。
阿禾并未立即启程。他在驿站井边住了三日,每日清晨摇铃三响,傍晚再摇五声,如同某种无声召唤。第四日清晨,一名十四五岁的少女徒步而来,背负竹篓,发髻散乱,眼中却有倔强光芒。她跪地呈上一只陶罐,内藏数十页手稿。
“我娘是泉州火灾中幸存的绣娘,”她声音清亮,“她临终前绣了一幅《百死图》,每一针一线都记着一个人的名字和死状。官府烧了她的绣坊,她把图拆成丝线,藏在嫁衣里逃出城。后来她教我识字,教我背那些名字……现在,我全写下来了。”
阿禾翻开手稿,指尖微微发抖。第一页写道:“天启七年四月十三,林氏阿娥,十九岁,读书人家女,火烧贡院时藏身井底,因窒息而亡。其兄曾为诸生,名列十罪书第三。”其后百余人,皆如此详述生平、死因、家人下落。末尾附有一诗,乃是少女所作:“井底幽魂不瞑目,年年春雨诉冤苦。若有青史重开日,请书贱名第三行。”
他合上册子,凝视少女良久,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大名,”她说,“我娘叫我‘小忆’。”
阿禾起身,从药箱底层取出一套素色布衣与一方砚台,交予她手中:“从今日起,你便是‘传声童子’。去湖南找苏井三,告诉他,泉州的声音,从未断绝。”
少女叩首谢恩,转身离去,身影渐没于山雾之中。
一个月后,洞庭湖畔,岳阳楼下。
阿禾立于舟头,望着烟波浩渺的湖面。苏井三已在此筹备多时,租下一整座书院旧址,召集湘、鄂、赣三省史录执笔者共八十九人,其中不乏前朝遗臣之后、罢官学士之徒。众人齐聚讲堂,争论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