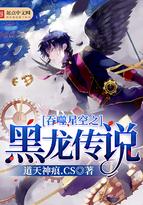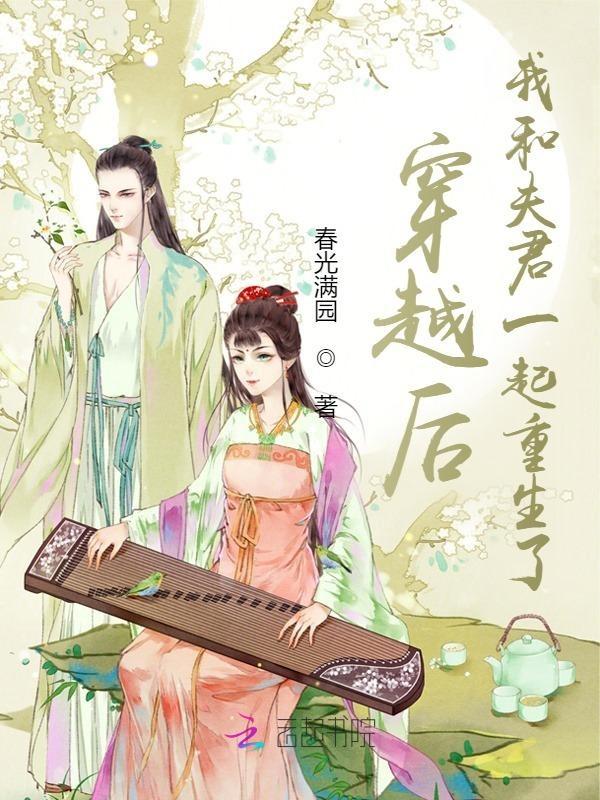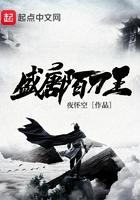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在现代留过学 > 第一千零七十八章 杨家将在交州2(第3页)
第一千零七十八章 杨家将在交州2(第3页)
老匠人摸索着铃身,指尖划过斑驳之处,忽然笑了:“这铃,是我师父铸的。当年共铸十四口,埋于十四处冤狱之地,名为‘井铃’,取‘深井藏声’之意。每一口铃,对应一段被掩埋的真相。铃响之时,便是亡魂开口之刻。”
“那……这枚为何残缺?”
“因为第十四口井,是活人埋的。”老匠人低声道,“耶律琚亲手将它埋入自己心口??他把自己也变成了井。所以这铃舌,是他割下的舌头所化。它不会发出声响,但能唤醒听见的能力。”
阿禾震撼无言。
老匠人又道:“如今,该铸第十五口了。”
“可是……朝廷严禁铸钟。”
“所以我不能铸。”老匠人意味深长地看着他,“但你可以。用笔,用纸,用脚步,用不肯闭嘴的嘴。你走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钟模;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铜汁;你点燃的每一次讲述,都是炉火。”
阿禾跪下,深深叩首。
离别那日,老匠人送他一段青铜碎片,说是当年“直言钟”的残片。“带着它,”他说,“让它提醒你??真正的钟,不在庙堂,而在民间。”
阿禾继续前行。他不再躲避追查,反而主动走向那些最黑暗的角落:边疆戍卒因举报将领克扣军饷而被活埋的沟壑;南方矿工集体中毒却被告知“瘟疫流行”的矿井;西北村庄因拒绝献女给权贵而遭“剿匪”屠戮的山谷……
他在每一个地方留下文字,组织讲述,建立野忆坛。他的《未载集》越写越厚,从一卷增至十卷。有人称他“游史”,有人骂他“祸根”,但他始终前行。
某夜宿于荒寺,月下独坐,他取出铜铃,轻抚铃身。忽然,铃身微热,一道极细的嗡鸣钻入耳中??不是来自外界,而是从他心底升起。
他闭上眼,听见了。
万千声音汇聚而来:有孩子的背书声,有农夫的号子,有妇人的哭诉,有囚徒的绝笔……它们交织成一片浩瀚的潮,冲刷着他灵魂的堤岸。
他睁开眼,发现铜铃表面浮现出一行细字,如血丝般蜿蜒:
>“第十五井,已在你喉中。”
他猛然醒悟??耶律琚留给他的,从来不是一件遗物,而是一种使命的转移。当一个人决定说出真相,他就成了新的井,新的铃,新的承载者。
他取出笔,在《未载集》第十卷首页写下新序:
>“史非金石所刻,乃血肉所书。
>井不在地下,而在人心。
>铃不在手中,而在喉间。
>我以身为井,以言为铃,
>不求惊天动地,但求??
>让下一个孩子,不必再问:
>‘为什么我们不敢说话?’”
写罢,他合上书卷,望向星空。
万里无云,银河如练。
他知道,甘兰进不会放过他,朝廷的追缉令已在路上,或许明日就有刀斧临门。但他不再恐惧。
因为他终于懂得,真正的历史,从不怕被烧毁。它会在一个母亲教孩子认字时复活,会在一个老兵醉酒后哼唱的歌谣里苏醒,会在某个雨夜,一个少年翻开残破书页时,轻轻念出:“若人人都怕说话,那沉默就成了最大的罪。”
而那一刻,新的井,又开始了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