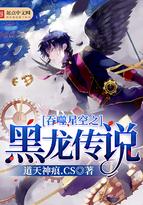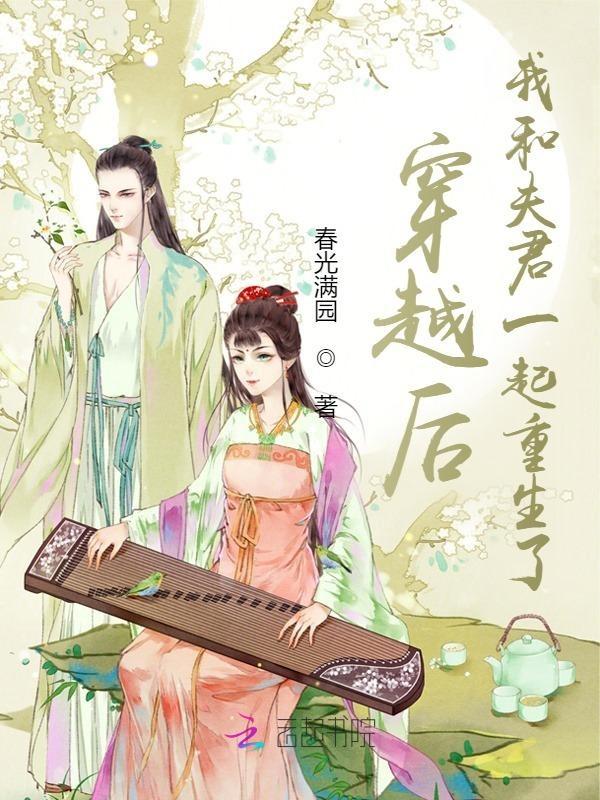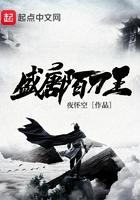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在现代留过学 > 第一千零七十八章 杨家将在交州2(第1页)
第一千零七十八章 杨家将在交州2(第1页)
喝着甘甜冰凉的荔枝饮,杨文怀舒服的哼了一声。
然后,靠在了用交州黄花梨打制的太师椅上。
屋内陈设,也是相当自然。
几面素雅的屏风上,绘着花鸟山石之景。
地上铺着的地毯,是汴京城。。。
海风在渔村的茅草屋顶上打着旋,把阿禾晾在竹竿上的《未载集》残稿吹得哗啦作响。他蹲在碑前,指尖抚过那八个发光大字,掌心仍残留着被雷电灼烧般的刺痛。村民们不敢靠近,远远跪拜,口中念着“天意”“神启”。可他知道,这不是天降奇象,是无数个沉默的夜晚、千万次欲言又止之后,终于有人肯将头抬起来看一眼天光。
他站起身,背脊挺直如松。十年行走,他早已学会在荒野中辨认真相的痕迹??不是靠神迹,而是靠那些藏在老人咳嗽间隙里的叹息,靠寡妇缝补渔网时突然停住的手,靠孩童无心说出的一句“爹死前说了一句话,娘立刻捂住了我的耳朵”。
碑立起来了,但话还远远没说完。
当晚,阿禾点灯抄录陈文昭的策论全文,笔尖不停,墨迹渐浓。窗外潮声阵阵,仿佛有无数魂灵踏浪而来,在屋外低语。写至“言禁一日不开,则民心一日不归;民心不归,则社稷如沙塔”时,毛笔忽然断裂,墨汁溅上纸面,像一朵绽开的黑莲。他怔了片刻,竟觉胸口发闷,似有重物压来。
就在这时,门被轻轻叩响。
三下,缓而轻,像是怕惊扰什么。
阿禾握紧铜铃,低声问:“谁?”
门外无人应答。他吹灭油灯,摸出匕首,缓缓拉开门闩。
月光下站着一个女人,披着褪色的蓝布斗篷,面容枯槁,唯有一双眼睛亮得惊人。她手中捧着一只陶罐,罐口用油纸封着,隐约透出腥咸之气。
“你是……柳莺儿?”阿禾迟疑道。
女人摇头:“我是她徒弟,姓沈。”声音沙哑如磨石,“师尊让我送这个给你。”
她将陶罐递上。阿禾接过,掀开一角油纸,一股海腥夹杂着腐朽气息扑面而来。他强忍不适,借月光窥探??罐中盛着半凝的海水,漂浮着几片焦黑的纸屑,还有半截炭化的手指骨。
“这是……?”
“泉州火狱的遗物。”沈姑娘低声道,“崇宁七年,朝廷以‘私议朝政’为由,将三百七十名书生锁入贡院,纵火焚之。当时师尊潜入废墟,在灰烬里扒出这些残片,拼了三天三夜,只复原出七句话。”她顿了顿,“其中一句,与你昨日发现的石片文字一模一样。”
阿禾心头巨震。他猛然想起陈文昭的名字曾在莆田老塾师口中一闪而过??“那是我师兄,考中解元,却因策论犯忌,被除名,后跳崖自尽”。
难道……陈文昭也曾在泉州参加会试?难道他的文章,早在那时便已被焚毁一次?
他颤抖着手从背包取出刚抄好的策论,对照记忆中的七句话??一字不差。
“这不可能……”他喃喃,“除非……他的文章曾两次现世,两次被毁,又两次……被人捡起。”
沈姑娘静静看着他:“师尊说,有些话,就像海里的盐,哪怕沉入深渊,终会被潮水带回人间。她还说,你要小心一个人。”
“谁?”
“甘兰进。”
阿禾一愣:“他不是和崔元朗一起推动忆堂设立的义士吗?”
“他曾是。”沈姑娘眼神冷了下来,“可权力一旦到手,人就容易忘记自己为何拔刀。如今他在京中掌‘守真士’名录审批,凡要录入《实录》者,皆需经他点头。他开始删改文字,压制不利朝廷的记载,甚至将当年揭发贪官的证人定为‘造谣惑众’,逐出忆堂。”
阿禾难以置信:“他怎敢?圣上亲颁诏令,史不可欺!”
“所以他做得极巧。”沈姑娘冷笑,“他说:‘为防奸人借冤案煽动民变,所有呈报须经三审。’于是层层设卡,能通过的,只剩些无关痛痒的小事。真正的大案,如军粮贪腐、边将屠民,全被压下。他还放出风声,说‘忆堂已成,不必再提旧事’,劝百姓‘向前看’。”
阿禾听得浑身发冷。他忽然明白??最可怕的不是禁止说话,而是允许你说,却让你的声音永远传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