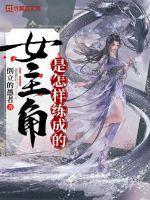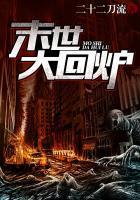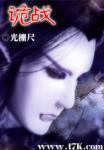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剑走偏锋的大明 > 第九百七十九章 不回头(第2页)
第九百七十九章 不回头(第2页)
命令即刻下达。三百精工昼夜不停,仅用七日便完成拆卸与包装。同时,胡澄派遣先遣队奔赴井陉口,在险要路段铺设临时木质轨道,设置绞盘牵引系统,确保重型部件顺利通过陡坡。
临行前夜,潘筠独自来到高炉广场。月光下,巨大的钢铁骨架静静矗立,宛如一座沉默的神庙。她抚摸着冰冷的立柱,忽然听见身后脚步声。
“你真打算亲自带队?”她问。
“必须去。”胡澄披着斗篷走来,“于谦信中说,上次鞑子劫掠蔚州,守军因火炮笨重无法转移,眼睁睁看着村庄焚毁。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机动防御’。”
潘筠沉默良久,终是取出一枚铜牌塞入他手中:“这是我让人打造的‘工程师徽章’,正面刻齿轮与尺规,背面铭文‘格物致用’。带上它,不只是为了身份识别……而是提醒你自己,你为何而战。”
胡澄凝视铜牌,轻轻收入怀中。
七日后,车队穿越太行天险,进入宣府地界。
一路上,他们遭遇三次“意外”:一次桥梁突然断裂,所幸提前探路避免坠崖;一次夜间营地遭蒙面人纵火,烧毁部分工具箱;还有一次,运送主轴的马车陷于泥沼,竟发现路面被人暗中泼油。
“又是喜宁的人。”胡澄冷声道,“他们怕的不是一门炮,而是整个战争模式的变革。”
抵达宣府城外军营时,于谦亲自出迎。两位老友相见,无多余寒暄,只重重一握。
“我已经划出五千步卒归你调度。”于谦道,“工匠食宿由神机营保障,所需材料优先供应。皇帝密旨:务必在雪封山前试炮成功。”
工地迅速建立起来。胡澄亲自指导建造新型铸造车间??采用半地下式结构,保温防寒,顶部安装可移动天窗以便吊装。炉膛使用耐火黏土与石墨混合砌筑,燃料改用焦炭,温度可达一千五百度以上,足以熔炼高碳钢。
与此同时,他带来的一支福州老匠团队开始制造“定辽炮”模具。这种新式火炮口径三寸,身管加长,内置膛线(虽为手工刻制,精度有限,但已具雏形),配用锥形弹头,射程可达两里,且不易炸膛。
最令人瞩目的,是炮座设计。传统的固定炮台笨重难移,而胡澄引入“轨道转向架”概念??将火炮安装在短轨小车上,通过人力或小型蒸汽机推动,实现三百六十度旋转与快速复位。
第十日清晨,第一门定辽炮完成总装。
校场之上,三千神机营将士列阵以待。风雪初歇,天地肃杀。于谦一身铠甲,立于点将台中央。
胡澄亲自点燃引信。
轰??!!!
一声巨响撕裂长空,炮口喷出烈焰,炮弹划破云层,准确命中三里外山坡上的靶标,巨石应声炸裂!
全场寂静一秒,随即爆发出震天欢呼!
“不偏不倚!”于谦热泪盈眶,“此炮若列阵十门,足以封锁一道关隘!”
更令人振奋的是,整套系统可在半小时内完成拆卸、转移并重新部署。第二次试射时,炮位已向左移动八百步,依旧精准无比。
当天夜里,于谦设宴犒劳全体工匠。酒至半酣,他忽然压低声音对胡澄道:
“你知道吗?曹鼐已在内阁提议成立‘稽查工商司’,专事审查各地工程开支,名义上防腐,实则剑指你我。更有传言,万妃欲借‘西苑暖房’一事发难,称你私占内库银两,图谋不轨。”
胡澄冷笑:“三千两建暖房,还不够某些勋贵一顿宴席。他们越是跳脚,越说明动了他们的根子。”
于谦点头:“所以我已奏请陛下,将‘定辽炮’列为军国重器,所有研发费用纳入兵部专项,不受户部节制。你的名字,也将记入《武备志》。”
“不必记我。”胡澄举杯,“记下赵四海、林小铁、潘筠、陈循……记下每一个流汗流血的普通人。历史可以遗忘英雄,但不能抹去他们留下的轨道。”
半月后,蒸汽动力原型机组装完毕,在校场进行首次牵引测试。一台小型蒸汽机带动绞盘,仅用六名士兵操作,便将十吨重的炮车拉动前行,速度超过牛车三倍。
消息传回京城,朱祁钰久久不语,最终批下八字:“利器在手,不可轻弃。”
然而,风暴并未平息。
某夜,胡澄正在图纸上推演“多级膨胀蒸汽机”构想,忽有卫兵急报:一名自称“福州林氏”的少年求见,声称有机密要事相告,且持有潘筠亲授的铜牌信物。
胡澄召见后,只见那少年不过十五六岁,衣衫褴褛,满脸风霜,却是眼神清明。他颤抖着从贴身衣物中取出一封密封油纸信,哽咽道:“我是林小铁……父亲是福州船厂焊工,母亲死于喜宁爪牙之手。他们杀了她,只因她不肯透露舱体焊接参数……我逃出来,走了四十天,只为把这东西交到您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