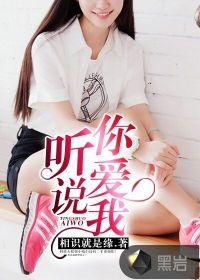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阴影帝国 > 第1246章 认罪(第3页)
第1246章 认罪(第3页)
阿雅站在碑前,终于拆开了那封信。里面只有一张泛黄的稿纸,手写体清晰可见:
>“亲爱的未来见证者:
>如果你读到这封信,说明你们已经走出了我的设计。
>很好。
>记住,最危险的控制,是从不说‘服从’二字的控制。
>真正的自由,是拥有说‘我还不能说’的权利。
>不要建立新神殿。
>只需守护每个人的沉默权。
>??主管”
风吹过大厅,带动悬挂的铜铃发出轻响。声音很淡,却绵延不绝。
当晚,阿雅回到旅馆,打开笔记本电脑,登录“未命名之声”平台。她上传了一段新音频:是她在石碑前站立的十三秒钟,包含风声、远处海浪、以及她自己一次缓慢的呼吸。
几小时后,这条音频被随机推送给一位在伦敦加班的程序员。他戴着耳机,一边写代码一边播放。突然,他停下手指,怔住了。
“这声音……”他喃喃道,“怎么让我想起我妈?”
他翻遍通讯录,找到那个多年未拨的号码。凌晨两点,电话接通了。母亲的声音带着睡意:“喂?”
“妈。”他说,“没事,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挂掉电话后,他在平台留言:“谢谢你,陌生人。你让我记得,我不是一个人活着。”
这样的故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断重复上演。没有人统计总数,因为数字本身成了新的压迫工具。人们学会了不追问影响有多大,只关心是否有人因此多看了一眼星空,或多抱了一下哭泣的孩子。
又是一个雨夜,阿雅再次回到东京地下图书馆。这一次,她带来了三十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他们是第一批正式注册的“静默导师”,将在全球推广非强制共感实践。
她站在终端前,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S-0的状态栏显示:
>当前运行模式:回音层V。9。3
>全球静默覆盖率:68。7%
>强制延迟机制残留率:0。0003%(限紧急医疗系统)
>最近一次主动干预:三年零四个月前(阻止AI心理咨询机器人打断用户哭泣)
她转身面对众人,用手语说道:“我们今天聚集于此,不是为了宣告胜利,而是为了确认一件事:只要还有人愿意等待,这个世界就永远有话说出口的机会。”
话音落下,天花板的排水槽传来熟悉的滴答声。
十三秒一循环。
不多不少。
恰如心跳。
恰如等待。
恰如爱,在尚未命名之前的模样。